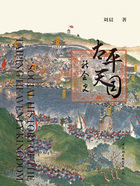
序一
一
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晨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研究》即将改名为《太平天国社会史》,公开出版,我很为他高兴。与当初作为显学相比,太平天国史研究已趋冷落。就在这种形势下,刘晨同志坚持研究,从《李昭寿平议》,到《萧朝贵研究》,再到《太平天国社会史》,十几年间成果频出。这种刻苦钻研、矢志不渝的精神,我是十分赞赏的。
二
读完这本论著,我认为主要有几个地方值得称道:
一是史料新。太平天国史的基本史料多达几千万字,阅读量之大远超一般课题。作者在充分研读基本史料的同时,还利用了一些尚未公布的稀见史料,像记太仓事的《避兵日记》,记吴江事的《黄熙龄日记》,记杭州事的《再生日记》《记事珠:咸丰庚申附辛酉日记》,记绍兴事的《劫难备录》,记苏州事的《胥台麋鹿记》,记常州事的《蒙难琐言》,记桐乡乌镇事的《寇难纪略》等,这些资料大多是作者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中查阅文献时发现的。作者还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资源。在资料上的另一特色是节选和考释了部分太平天国时期慈善家余治绘的《江南铁泪图》,作为论述的图像反映和史料旁证。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需要作者有深厚的史料功底,不仅需要有发掘史料的敏感、编排史料的技能,还要有对史料和史实的考辨能力。作者重视考辨史料、考据史实,充分发掘利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史料,在研究中就一个问题旁征博引,反复论证,正如罗尔纲先生提出的,历史学家需要具有一种“打破砂锅璺(问)到底”的精神,这就保障了课题研究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二是视角新。历史学家应该兼具文献学家的实证功夫和哲学家的思辨精神。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过去的学者,基本上没有关注“反抗反抗者”的历史,缺少系统阐述民众与太平天国复杂关系的另一面——对立层面的表现、成因和影响。这一问题富有深意且耐人寻味。这对全面、客观评价太平天国也极有必要。作者指出,他立足民间,关注下层社会,试图构建民间视角下的太平天国史。这也是建立在对太平天国研究的学术史充分掌握并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过去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除已有的李文海、刘仰东二位先生的《太平天国社会风情》等论作以外,研究仍然不足。太平天国民变的研究实际上涵盖了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作者对这一研究空白,作了初步探讨,深化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从全书论述看,作者的旨趣基本达到。
三是方法新。全书在方法论上一个比较显著的特色是对江南地区的民变、田赋、地租、杂税、人口、土地等大量数据进行了系统计量考证,在此基础上对获得的知识做进一步的分析、解释,将感性知识向理论的高度升华。再就是运用了比较研究法,例如将苏南前后期民变、同期太平天国统治区和清政府辖区的民变进行比较,江南民变构成要素的统计比较、具体案例的比较等,视野比较开阔。再就是多角度写作的方法,将总体与个案研究结合、宏观叙事与微观分析结合,全书既有个案的细腻分析,也有宏观的深入研究。作者还对本书的叙事时空进行了延展,以太平天国为研究主体,却不局限在太平天国,将长时段、大历史观同微观时段相结合,按照太平天国历史演变,展现了一幅晚清时期江南地方社会发生危机的全景画,从而避免了写成民变的专史。这些都是该书在方法论上的闪光点。
四是观点新。作者据史直陈,考察细致,所得观点较为新颖且经得起推敲。例如,作者通过比较分析观察到:19世纪60年代“天国”民变迭起可以看作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对立关系的延续,清朝时期日益尖锐和复杂化的社会矛盾在太平天国新政权建立后由于主客观环境、传统和新兴因素的影响,呈现了愈演愈烈之势。所以,“天国”民变各要素既有前朝传统的延续性,又有战时太平天国自己的特殊性。对于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天国”民变诸要素、太平天国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形态。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众反抗,是国家权力不当控制地方的直接反映。一般来说,民变与太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程度和干预介入基层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愈是太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地区,民变的数量愈多,规模愈大,烈度愈强。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并不完全形同孔飞力先生指出的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态势,太平天国时期的绅权可能不同程度不同地域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这很有见地,特别是民变反映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越是在国家权力控制薄弱的地区越易滋生民变,而恰恰是在国家权力过度不当控制的区域。另外,像作者归纳的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分布的主要地域特点:苏南多于浙江,市镇乡村居多,以及对太平天国“自立自办团练”、“治理土匪”、太平天国时期的“谶”和“巫术”、太平天国时期的“恐慌”、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等问题的探讨,都具有相当的新意和深度。
要准确深入地认识历史,还必须具备宽广的知识结构。作者则能注意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联系,从更广阔的角度观察太平天国历史,例如作者在研究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时认为,“战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影响”;又如他在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时指出,“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分析,战争的客观影响具有某种进步意义。太平天国战争对晚清政局、江南社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客观影响,极大地改变了近世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更多的近代性元素,战后近代化格局也奠基于太平天国”。这可能更接近于历史实际。这些观点的得出说明作者的知识储备足够宽厚,才能洞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上下、左右、前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才能既了解民变的“前因”,又了解民变的“后果”,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能够延展叙事时空,以比较视野观察晚清民变,提出有见地的观点,也说明了这点。
五是立论公允。现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出现了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两个极端,人们的看法分歧较多、争议很大。实际上,两个极端都是不科学的。因为,这违背了历史研究最高层次,亦即基本的指导思想,也是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应该辩证地、全面地去看,不能为求所谓“创新”而违背历史研究者的“德性”。难得的是,作者研究太平天国的“负面”现象,却没有得出一味否定太平天国的结论,全书的论说重点是放在分析民变的成因、民变对太平天国的影响,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民心”所向和转向对一个“革命”政权要保持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作者以太平天国的民变和部分平民领导的反太平军武装起义为切入点,全面分析了民众与革命辩证统一的整体关系,进一步提出评价革命功过是非,须客观理性立足史料和史实,绝不能泛泛而谈。正是作者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史学研究,才保证全书总体上立论允当,他从太平天国稳定社会秩序的努力、推行社会战略的尝试,以及在地方社会事务中的“变通”原则等方面立论,最终肯定了“太平天国作为中国旧式农民运动最高峰的历史地位”,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
六是具有现实关怀。民变研究本身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最大规模的“民变”,“革命”政权竟也激发了它治理下的“民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具现实关怀。民变研究关系到国家治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该书研究的民变,实际主要是乡村民变,它又涉及农村与农民、流民、村霸、黑恶势力、邪教、腐败等基层社会秩序的种种问题。这一研究的推进并成功出版,可为现实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这正体现了作者是以入世的情怀“做学问”。当然,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想要成就一番事业,还要以出世的情怀做人。我经常讲,要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也要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这就是人生哲学的问题。我知道,本书的作者即是这样一位专心致意、心无二用,能够“坐下来、钻进去”的青年学者。回顾以往,我的两位老师陈恭禄先生和罗尔纲先生,他们一辈子读书、写书,专心学术,不计个人是非荣辱的高尚精神境界,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希望刘晨秉承前辈学者的学术风貌,能够将这种入世治学和出世做人相结合的情怀,坚持下去,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哲学水平,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再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三
人的认识具有相对真理性,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辩证发展的过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过程。我个人认为,这本论著也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或者深化研究的问题。
其一,作者将研究对象框定为主要由经济肇因,带有自发性、突发性,特别是与清政府或清军没有直接组织联系的民变类别。因为这类民变所展现的太平军与民众的对立关系内涵具有特殊性和说服力,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将民变与所有“团练”形式的对立武装划清界限。我认为,苏浙地区的团练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清朝政府组织和领导的团练,二是政府督办的地方民团,三是地方人士主动组织的防卫武装。其中第三个类型的“民团”也符合作者框定的民变类别。我认为可以将其加入民众反抗太平军的案例中,在抗争类型上稍作区分即可,这样既可以丰富研究对象,让“天国民变”这一历史现象的形象更加丰富起来,也可以充分说明问题,同时还能避免概念分歧,无须纠结于案例是否具有明显的政治权力意识或诉求,“民变”的部分诉求也可以是政治性的。我认为,陈旭麓先生界定的民变是以下层社会为主体的群众“用直接诉诸行动的方式以表达自己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反抗”较好。正是研究对象框定的相对局限,像作者观察到的非常有价值的三起“平民”领导的武装案例——包立身、沈掌大和“盖天王”,本来极能说明“对立”的问题,却只能作为民变的参照简单论述。对于包立身的事,我曾在《太平天国通史》中提到,作者则另有专著专论。作者曾对我提到,要利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深化太平天国时期“民众对立”的另一大类历史现象——太平天国时期团练研究。这很好,可以弥补本书的研究缺憾。
其二,作者突出强调民变的社会背景,即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主要是经济政略,通过太平天国应对民变的政策政略等问题反映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并指出社会战略的失败,预示着太平天国失败的最终结局,这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作者对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军事占领的背景的关注还不够。实际上,太平军占有苏南、浙江,一切政略政策的重心均置于征收粮饷军需,满足战争和物质需求。相当数量民变的发生是与太平军穷竭民力、滥征乱收、太平天国政治腐败有直接关系的,这些恐怕不仅是经济问题的范畴了。
其三,将晚清江南民变与太平天国占领区的民变进行比较,其新意上面已经提到。我认为还有两个地区可以与江南民变深化比较研究,那就是湖南和广西,广西是太平天国的策源地,湖南是太平军迅猛发展的地域,这两个地域的民变与太平军兴的关系颇值研究,可以深化对太平天国历史背景的认知,民变在数量上、在程度上在这两个地区也具有代表性。
近期我看到了国家清史工程出版的《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对后期太平天国照旧收税,地方经济职官,捐费与役,太平天国境内的抗租、抗粮、抗捐相关条目的资料作了简要编辑,这和这本专著的论说内容有相关性。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出版,特别是由罗尔纲先生奠基整理的《太平天国史料汇编》工程的推进编纂,我相信,像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这类新的研究领域还可以继续研究,太平天国研究还大有可为。
鉴于历史研究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质,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对自己的观点还是对他人的观点都应该持有这种态度,应该首先寻找既得成果中存在的错误,这样才能逐步向绝对真理靠近。所以上面罗列的意见也不会影响到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我仍然认为,这本书是太平天国史领域近年来较为少见的优秀研究成果,推动了太平天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四
该书的作者刘晨与我是忘年之交,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现在,我个人已92岁。岁月的增加使我领悟到一个值得重视的道理:年长学者热情帮助年轻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取得教学相长的结果,加强年长学者的实证功夫和思辨精神。所以,我非常乐于见到并且会帮助他在学术道路上进一步成长。我知道,他痴迷于太平天国史研究,除了这本书,他目前还在效法前辈学者致力于一部“太平天国史”的写作,并且进行着“太平天国史译丛”的编译工作;他还跟我讲,希望利用新发掘的史料在我所撰《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的基础上,重新校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我都予以鼓励。我当时在该书的“后记”部分就曾写道:“甚望若干年后有《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之校补》问世。”现在终于有人勇于承担这项重任。刘晨现今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且还很年轻,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期待着他取得更大的成就。
茅家琦
2018年5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