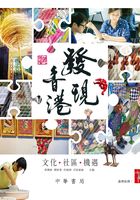
社區留屋留人留情,藍屋「活保育」創佳話
我離開了灣仔區議會已經四年多,回顧我十多年從市政局到區議會的生涯,讓我難忘的一件事,就是改變了灣仔藍屋的命運。
灣仔藍屋在石水渠街,它現在有了保育和再生的機會。發展局轄下的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本已與未來的營運者聖雅各福群會開展工作,但是,原方案並非如此。在2006年3月31日,房屋協會宣佈活化藍屋計劃,表示那裏將會是主題旅遊點,有茶樓、中醫藥及水療。但有一點居民很不願意,就是原方案要求業主及居民必須搬走,不可再在那裏居住。原方案想將藍屋以純商業的角度營運,但這跟藍屋的歷史不符。藍屋一向有商有住,那裏有大家熟悉的林鎮顯醫館,盛傳是黃飛鴻徒弟開辦,也有民居。藍屋為什麼是藍色呢?是因為藍屋原是屬於地政署的,地政署每隔數年就會翻新藍屋的外牆,而聽說當時在倉庫裏最多的是藍色油漆,於是原來是灰色的外牆就變成藍色了。
藍屋的歷史多姿多采,灣仔第一間英文中學曾在那裏創辦。那裏有很多居民住了很多年。要做活化的,除了藍屋,還有黃屋及橙屋,詳細我不說了。面對這個原方案,居民和社區團體可以做什麼?會否只是接受,叫居民遷走,然後把藍屋變成水療中心?當時我還是灣仔區議會主席,我們認為應先做一個保育藍屋的研究報告,發掘故事,然後讓整個社區有跨界參與,過程大概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參與規劃;第二部分是推動新的倡議策略;第三部分是做國際案例研究;第四部分是居民的共識。其實這就是剛才伍婉婷提到的社區營造,也有如馬逢國議員剛才所說的,工業大廈也可改變成室內足球場;我們這一群人就覺得也許可以改變政府的想法,但居民的認同是最重要,因為我們談的是社區文化。
我們想建立社區的認同,但我們要用一個怎樣的過程令居民明白這件事,讓他們自己也可以發聲?在聖雅各福群會的協助下,專業人士、學者、文化界的朋友和街坊成立了藍屋保育小組,用創新的參與方法,令居民明白可有多種方法活化藍屋,但不需要全部居民搬走。如果他們想搬走,當然可以;但不想搬的可以留下來。這小組動員了社區的網絡,花了近三年時間與街坊溝通。藍屋保育小組是跨界別的,有老人家、年輕人、社工,還有專業人士,如建築師等。居民熱烈參與,組成小組反思:街坊住了藍屋那麼久,其中一位住了五、六十年,如果政府要活化這地方,為什麼他們要搬走?可不可以「留屋兼留人」呢?於是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討論,當中有些居民打算搬走,也有些居民決定留低。這個漫長的參與規劃過程,也是一個社區營造共識的過程,雖然時間長,但我覺得總比一個分化的社區好。
跨界參與不容易,大家經常在藍屋的故事館開會開到很晚。第一階段是令居民明白到他們原來是有選擇的,他們可以選擇留下來。第二階段,就是做口述歷史,發掘社區特色。這套方法其實每個社區都適用。灣仔石水渠街就有很多有趣故事,例如藍屋戰時住了很多人,大家走難來到灣仔,在藍屋住下來,有個街坊說在露台睡覺都可以。因為當時環境是擠迫得連露台也可以住上幾個人,但大家卻相安無事,好像「七十二家房客」一樣,求同存異。這些口述歷史很多,之後就產生文化旅遊的念頭。
大家應記得近年灣仔有很多這類文化旅遊,帶人遊走不同舊社區,看鬼屋,聽鬼故。當時聖雅各福群會鼓勵街坊作導賞員,晚上走到船街紅屋講鬼故,引起傳媒注意,不用求記者來採訪,報紙也主動大肆報道,將灣仔的故事和特色提升到傳媒層面,增加曝光率。此外,街坊又認為藍屋好像一座古堡,於是他們請設計師將藍屋設計成古堡,再製成單張派發。
第三階段是找學術界一起研究國際案例。例如西班牙的巴塞隆拿有很多舊區與香港有點近似,卻總是有人想把它清拆。其中一個在1930年興建的舊區,當地政府想清拆,但居民反對,不想搬走。於是居民走出來,不是與政府抗爭,而是營造共識,營造一個可達致雙贏的社區。學者協助我們找了案例支持活化藍屋,讓居民留低。經過兩年的醞釀,居民終於決定向發展局提交一個「藍屋活保育」方案。「活保育」的意思是:明明藍屋是活的,而居民都是活生生的,因此要用尊重生活和尊重居民的方法進行保育。
2007年10月的某個星期天,是歷史性的一天。那天只有原居民留在藍屋,社工和專業人士等都沒有出現。當時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就在那天落區,居民親自告訴林鄭局長,他們住了藍屋很久,很喜歡這裏,雖然藍屋沒有洗手間,但翻新時加建洗手間不就可以了嗎?我們不必搬的呀。為什麼你不讓我們留下,加強這裏的社區網絡?之後他們就提出「活保育」計劃。
林太聽了後,應該有些新的想法,因為隔沒多久,她就改變了方針。房協和市建局後來退出了藍屋計劃,藍屋更被納入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原來這個參與的過程可以開花結果,首先營造共識(有人想走就走,有人想留就留),然後用文化導賞和國際案例提升曝光率,到最後向林太報告,她竟然覺得可行,表示支持。得悉這結果後,居民都很開心。
但之後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徵求意見書的過程歷時數年,由陳智思領導的活化歷史建築保育小組經過數輪評審,最後在2010年由聖雅各及藍屋保育小組的主要成員取得經營權,「活保育」計劃現時被稱為「we嘩藍屋」,獲發展局的復修款項5,600萬元,居民日後可參與管理。事件就說到這裏。那藍屋活化後會有什麼呢?它將有社會企業,繼續發展故事館,發掘社區故事,由街坊舉辦導賞團,用文化旅遊的方式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