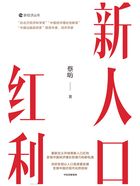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宏观目标是以更高的人口整体素质,适度的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内涵的人口高质量发展。
人口均衡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口发展显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是人口发展不均衡的诸多表现。基于1982年、2012年和2023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不同年龄组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一是0~14岁儿童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在这三个年份分别为33.6%、16.5%和16.3%;二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到峰值并越过转折点后迅速下降的倒U形轨迹,在这三个年份分别为61.5%、74.1%和68.3%;三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提高,在这三个年份分别为4.9%、9.4%和15.4%。
此外,各地区在人口格局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并且同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密切相关。2022年,我国大陆22个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之间的人口分化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产生5.8‰~8.8‰的悬殊幅度,老龄化率则有5.9%~20.0%的高低差距。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老龄化率都是人口转变的结果和人口格局的表现,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而两者密切相关。例如,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老龄化率之间有高达-0.883的相关系数。人口格局也与经济发展具有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如区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889。
因此,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既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主要内容,也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具体来说,在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两个要求之间,表现为一种递进的关系,理解两者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人口发展新常态及其挑战,最直接表现在人口发展的一系列不均衡结果及不可持续因素上,反映在包括生育水平、年龄结构、数量与素质、区域格局,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等方面;二是由于人口发展质量正是孕育于上述这些方面,所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与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在手段和目标上高度一致。旨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努力,包括推动形成适度生育水平以稳定人口规模、形成经济和社会合理的人口区域分布、培育与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正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进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必由之路。
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为重点
人口的现实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每个时期的人口特征都由以往的人口转变所决定。因此,人口现状可以说是过去人口变化的回声。我国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在从1960年人口负增长中得到恢复的过程中,1962—197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20‰以上。随后便出现对应这一婴儿潮的人口回声。第一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儿童人口的数量增长和比重提高十分迅速,直到80年代才趋于减速。第二波,1980—2010年,年轻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增长和比重提高十分迅速,形成了“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有利人口结构,为这一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特殊的源泉——人口红利。第三波,以年轻劳动力开始更快增长的年份为基准,经过三四十年,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经历一段时间负增长之后,老年人口的数量增长和比重提高显著加速。正是以这个人口回声效应为参照,《决定》做出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重要部署,特别从以下方面强调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着眼点和发力点。
首先,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这个更替水平上,不仅是保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也是在理想条件下家庭所期望的孩子数量。然而,从极低生育率向这个水平回归,受到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生育率在低水平长期徘徊后回升到更替水平,国际上几乎没有先例。但我们仍可促进生育率向这个方向尽可能靠近,例如,按照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设想的水平,即到2030年总和生育率达到1.8应该成为政策目标,并引导家庭以行动响应。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政府推动形成体系和完善机制,明显加大政策支持和激励力度,通过家庭与社会的激励相容和共同努力,促进总和生育率回升到更可持续的水平。
其次,着眼全生命周期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培育和发挥新人口红利。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在实践中产生于特殊的人口转变时期,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人口,进而形成人口抚养比低且持续下降的格局。可见,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与特定的人口结构特征相联系的。一旦这种年龄结构不复存在,传统的人口红利支撑的增长动能随之减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广义人口红利的消失,或经济增长从此失去动力。以转换认识范式为前提,重新定义并着力培育人口红利,即通过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实现托幼一体化、延伸义务教育和国民教育、鼓励终身学习和职业培训等,提高所有年龄组人口的综合素质,完全有机会形成新人口红利,为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提供支撑。当然,这还要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为条件,着力解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使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最后,完善政策机制,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于2023年达到12 614美元,在到2035年达到24 000美元的发展过程中,我国老龄化率始终高于这个发展阶段上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未富先老的特点。因此,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既明显增进老年人福祉,也充分发挥老年人庞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力,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
用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期
人口发展新常态既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孕育着新的机会,必须牢牢把握机遇。从现在起到2035年,对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说,是一个不应忽略的机会窗口。一方面,我国经济仍有潜力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根据对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在2035年前,我国经济能够以年均4.7%的速度增长。这可谓一枝独秀,因为无论是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老龄化率所表示的人口转变阶段来看,鲜有国家在相同阶段能够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这足以保证有充足的资源,支撑实施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战略。
经济总规模能够以较快的速度继续扩大,确保我国的投入增长足以支撑人力资本的加速培养,以及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持续提高。例如,我国在公共教育支出和研发支出方面都保持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特定比例,因此,保障经济总规模的继续扩大,相应的投入即可做到水涨船高。此外,出生人口和儿童人数减少和比重下降也导致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例如,在2035年前,17岁以下儿童和6岁以下儿童都将以年均3%的速度减少,意味着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资源约束大幅度减弱。经济的增长和儿童人数的减少两个趋势同时存在表明:一方面,以往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基础和创新能力的存量将进一步释放;另一方面,培育和增强这些发展因素增量的保障水平也在提高。所以说,这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难得的机遇,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利窗口期。
这个窗口期对于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要求明显扩大资源的投入。这个窗口期的核心就在于,我们可以指望一个负担趋于减轻、资源相对丰富的发展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在我国目前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公共品边界显著得到拓展,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表现出大幅增长的特征,政府通常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并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这个一般趋势在我国的体现与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要求和做法高度一致,也将经过大体相同的实现路径。从时间上说,这个机会窗口既非永恒也不会长期延续,因此必须清楚认识、牢牢把握和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窗口期,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在应对少子化、老龄化挑战的同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一方面,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显著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高速增长时期,得益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这两次教育大飞跃。培育新人口红利也需要一个同等幅度、同等效应的教育飞跃。相应的改革着眼点在于提高受教育年限,以及教育资源的更充分投入和更均等配置,让城乡所有年龄段人群都获得以基本公共服务形式提供的优质教育。特别关注学前教育、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等保障机制,逐步扩大以义务教育阶段为重点的免费教育范围。
另一方面,提高城乡基本养老的保障水平、普惠性和均等化程度,增进全体老年人福祉。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提高这个体系功效的重点在于补足现存的体制机制短板和缺项,通过改革缩小乃至消除既有的覆盖水平的缺口和保障水平的差距,特别着眼于提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等化程度。与此同时,增强各种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之间的整合性和互补性,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统一、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从全生命周期形成稳定、良好的预期,提升生育意愿,老年人口获得感与民生福祉同步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