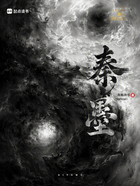
第4章 闲月
大雪时节有大雪,可燕北的雪最是吃人。
距离东城门刺杀事件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了。
整个燕下都的百姓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个欺横霸世的小恶棍了。
有些人闭着门偷着乐,心喜那祸害恐怕没死也该残了,再也不好出来欺横霸市了,真是多亏了太子殿下为民除害啊。
可几家欢喜,几家愁。
两年前,那位长相俊朗的公子哥说要去辽东赏琉璃世界,在一众莺莺燕燕的左拥右抱下出了武阳城。
自那之后,那个冤家从此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出现在武阳城大小头牌的闺房和各方纨绔子弟,私下的嫉妒憎恶之中了。
以前的六国客商谁不知道,燕国美女冠绝天下,燕下都武阳就有一间天下最好的女闾。
背后的东家是谁不清楚,倒是起了个风雅出尘的名字:长夜楼,寓意夜夜承欢,长夜禁明。
楼内多数倡女都颇有文才,能吟诗善画,精七国书工,善绘兰手谈,通鼓琴音律。
可当那位只喜欢听曲调情,为了习武不敢泄了童子之身的公子哥离开武阳后,再也没人能镇得住那些五大三粗的兵痞游侠儿了。
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横货,哪懂的半分怜香惜玉,每次下来,姑娘们可不都被折腾的像是被拔了毛的野鸡?
久而久之哪还有什么只卖艺,不卖身的清高说辞,这座流金淌银的长夜楼也开始做起了那位公子最不喜的皮肉生意。
据说在三六九等的各色倡女中,光长相出挑还不行,必须得懂琴棋书画,如此才能算的上是极品,这种极品遇到出手阔绰的贵族子弟,怎么都得出到千金以上。
不过这还不算最好,最好的莫过于东胡女子。
倒不是说燕地女子姿色不够好,主要还是各色差异太大,长相秀美的可人儿的确是不少,但长相奇葩猪猡的也有一箩筐,远没有东胡女子那般匀称,关键还够劲儿!
还听说与普通倡女这种广受文人喜爱的婉约派不一样,调教妥帖好的东胡女子,具是能让勇猛悍卒都虎躯一震的存在!
毕竟匈奴也好,东胡也罢,哪个不是民风彪悍到骇人?
而且那些逛女闾的糙汉子们,哪里懂什么情调,抓紧消遣放松一下就完事了,可哪一个又不是扶墙而出,脸色煞白呢?
可恨这些姑娘们,每日都在闺房里暗自垂泪,念着那位能救他们于水火的公子哥儿到底在哪呢?
……
坐落在燕下都核心位置的秦家大宅,直至入夜,还有一处以八卦为基而建的楼阁灯火通明。
楼分五层,并不如何雄伟魁绝,也无雕梁画栋,更无金碧辉煌,很普通的一座楼阁,可飞檐翘角上挂满了兵戈铜铃,有风雪袭来,更有肃杀之音响彻寰宇。
有人说那是雪的声音,也有人说那是血的声音。
更是当年秦开秦老将军带领三百悍卒一路砍杀,为大燕扩地千里,拥坚兵十万之众生死相随,最终却客死在齐国火牛冲阵下的绝望哀号。
总之它现在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听雪楼。
“今天府上倒是安静,我那个弟弟今儿没变着法子的逃跑吧?”
申屠阿茶笑着接过秦虞手中的汤药道:“前些日子爬墙、钻狗洞,还做了个大风筝想要飞出去,不过被我一箭射了下来,在床上躺了三天,倒是安生了许多。”
秦虞掩嘴偷笑,却不敢大声,生怕又要咯血不止了。
“虽然是安生了,但现在又不知道在屋里研究什么坏点子呢。”
“研究什么?”
“好像让人买了许多药材。”
“药材?”秦虞黛眉微蹙:“他还懂用药了?”
申屠阿茶无奈的摇了摇头:“以前倒是不觉得他有这般多的鬼点子。”
身体有疾的秦虞一笑无语。
“罢了,随他去吧,只要不到处生事就好。若是出府,派人跟着便是。”
“喏。”
翌日。
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
彻底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医学博士,成功跻身为战国一员的秦舞阳今天心情不错,一大早便换上了燕地特有的装束,辫发高束成马尾,有古银色发环装饰,整体给人一种慵懒而又高贵的复杂气质。
此刻正身披一件墨色大氅,斜靠在栏杆处,望着阿姐秦虞所在的听雪楼,怔怔出神。
“你们说公子在饔和飧之间加了一个午餐也就罢了,昨个儿又非要加一个什么下午茶,说正规公司里的牛马都有下午茶的,牛马我知道,可公司是什么东西?”
“或许不是个东西呢?”
一帮视力极好的怀春女子,正躲得远远的看着那位比燕国任何一个男子都要好看的公子,叽叽喳喳吵嚷个不停。
“总觉得公子从辽东回来以后,就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也不乱发脾气了,我还多少有些不习惯嘞。”
那丫鬟小脸羞的通红,引来一众莺莺燕燕打趣嬉笑。
“我看你呀,就是个小浪蹄子!”
“跟你们说,昨个儿夜里我当着公子的面不小心打碎了一件青瓷,公子非但没有打骂,还摸着我的手说什么十指尖如笋,腕似白莲藕,你们听听,这是不是在夸我呢?”
那丫头脸颊同样绯红,可忽的又苦恼了起来:“就怕只是做了一场梦,梦醒了,这般好的公子又要消失不见咯。”
几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表情实在精彩,时而欢快,时而苦恼,就像是想要留住什么,又害怕失去什么。
可她们哪里知道,之前的那个混世魔王,早已死在了一个月前的雪夜里。
舞阳贴身丫鬟奉萤,看着几人又在背后乱嚼公子舌根,插着小腰,没好气道:“还不快去干活,小心我告诉单管家,让你们挨板子!”
小丫头约莫这几日心情同样不错,整个人气色都好了许多,就连说话都变得铿锵有力了,水灵灵的眸子眼瞅着几个婢子灰溜溜的跑开,才喜上眉梢,一路朝公子小跑而去。
“公子,你差人定制的银针送来了,铁匠说已经尽力拉到最细了,快看看合不合适。”
作为公子的贴身婢女,奉萤最是知道自家公子这段时间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总爱说一些奇奇怪怪,又离经叛道的言论。
比如什么无论男女,人生而平等,没有贵贱之分,没有高低之别。
难道那些大儒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爱有差等,礼有尊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兄友弟恭,你父亲一定比你尊贵,你爷爷一定比你父亲尊贵,贵族一定比士人尊贵,士人又比平民尊贵是秕言谬说?
奉萤不敢细想,总之自己做公子一天的奴婢,便是公子一辈子的奴婢,他以前坏也罢,现在好也罢,自己这条命都是公子的。
就是盼着公子,可莫要再拉着自己同案飧饔的好,自己这种卑贱的奴婢如何受的起?
秦舞阳笑着接过奉萤手中的银针,满意的点了点头。
“不错,刚好合适。”
上辈子针刺所用的针一般在0.25毫米左右,甚至比一般成年男性的头发还要细,没想到这里的工匠居然也能将银针拉伸到这种精度。
其实针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使用尖锐的石器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缓解疼痛,这算是针刺医学的基本雏形。
从《黄帝内经》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针砭、火、酒、热熨等已广泛用于治疗疾病,《难经》和《伤寒论》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针刺理论和实践。
而后世总有人误以为针刺和针灸是同一种东西,可两者不能说是南辕北辙,但针刺和艾灸的确不是一回事。
“公子,这么细的针一扎就断,如何能缝制衣物呢?”
秦舞阳笑道:“银的延展性很强,不会轻盈折断的。再说了,我又没说要拿它来缝衣服。”
“不缝衣服?那要它何用?”
秦舞阳不怀好意的盯着奉萤道:“许久没扎针了,不知道手艺生疏了没,刚好拿你练练手。”
眼看着细针就要朝自己扎来,奉萤明媚的眸子瞪得溜圆,竟要作势跪倒在地,哽咽道:“公子不要扎奉莹啊!”
秦舞阳眼疾手快,一把将小丫头搀起来:“怕什么,本公子的银针是孙思邈的针,不是容嬷嬷的针。”
小丫头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奉萤不知道什么孙思邈,也不认识容嬷嬷,只知道十指连心,被针扎一下可疼可疼了。”
一边说着,一边还露出了枯瘦的手指,只见奉萤中指和无名指甲上各有一条刺目淤痕。
“这是……我扎的?”
奉萤怯生生的点了点头。
秦舞阳皱着眉头,暗骂了一声畜生啊。
不过倒也并没有出声安抚,既然现在自己成了秦舞阳,这样歹毒的事情就绝不会再发生了。
虽然自己没有那么高尚,既贪生,又怕死,还爱美人也爱财,但不说做个积德行善的圣人,可最起码做人得有底线。
总不能像那个发明美人盂、美人纸这种违背伦理道德的纨绔子弟吧,那自己岂不是对不起祖国的九年义务教育?
不过身为贵族子弟,平时揩揩油不过分吧?
于是摸了摸奉萤的小手,一本正经道:“你一定是记错了,我怎么能干出这么混蛋的事呢?”
奉萤现在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现在只想远远躲开这个笑也迷人,不笑也醉人的无良家伙。
“你是不是最近总感觉头晕目眩,有时还昏昏沉沉,身体困乏无力?”秦舞阳认真问道。
小丫头该多想的时候不多想,不该多想的时候倒想得挺多。
难道公子是看到自己偷懒了?
一边想着一边又扑通跪倒在地,惊慌失措道:“奉萤不是有意要偷懒的,奉萤知错了,奉萤以后一定少睡觉多做事,公子就莫要扎我了。”
秦舞阳抽了抽嘴角:“什么跟什么啊!”
“总之,你这个毛病就是因为长时间久跪,然后总喜欢低着脑袋不正眼看人,导致脊椎压迫神经,从而引发的脑供血不足。”
奉萤低头不语,她一出生就是婢女,没什么文化,平时也只有去府中听雪楼,帮小姐收拾简牍时,才能听小姐对着一株甘棠说几句什么: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她听不懂这个召伯到底在说些什么,更听不懂公子说的什么压迫神经,脑供血不足的天大道理。
总觉得自己之所以困乏,是因为睡的太少了,毕竟眼前这位少爷这两天可没少折腾府中下人,大半夜不睡觉去钻狗洞,可曾听闻这种千古奇闻?
所以半夜也得待在旁边看着,马虎不得。
看着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的奉莹,秦舞阳故意恼道:“你知道吗?在我们那不正眼看人,会被视为无礼的。”
“所以,快抬起头来!”
小丫头被唬的全身一颤,俏脸如小鸡啄米般,怯生生的瞟了一眼秦舞阳,又大呼一声奴婢该死,跪了下去。
秦舞阳猛拍脑门,长叹了一声。
果然,当沟通双方的思维和见解不在同一水平线时,那么这场沟通将毫无意义。
“算了算了,快起来吧。但你既然是我的奴婢,那就乖乖的让我扎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