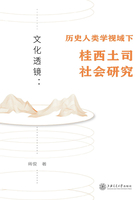
一、瘴的地理学解释及其背后
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瘴”至少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是指“瘴气”,意为有毒的气体。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已对瘴气的形状有了初步的描写:“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 明代邝露的描述更生动:“瘴起时,望之有气一道,上冲如柱,稍顷散漫,下似黄雾,空中如弹丸,渐大如车轮,四下掷人,中之者为痞闷,为疯痖,为汗死。人若伏地,从其自掷,则无恙。”
明代邝露的描述更生动:“瘴起时,望之有气一道,上冲如柱,稍顷散漫,下似黄雾,空中如弹丸,渐大如车轮,四下掷人,中之者为痞闷,为疯痖,为汗死。人若伏地,从其自掷,则无恙。” 清人陆祚蕃《粤西偶记》云:“天气炎蒸,地气卑湿,结为瘴疠,危害不少,有形如云霞、如浓雾,无形者或腥风四射,或异香袭人。”
清人陆祚蕃《粤西偶记》云:“天气炎蒸,地气卑湿,结为瘴疠,危害不少,有形如云霞、如浓雾,无形者或腥风四射,或异香袭人。” 道光《上思州志》所载十分细致:“邕(州)去桂千余里,属介边之区,大都暑多寒少,晴则热,雨则寒。一日之中,气候倐易。至其深山密菁之间,虫蛇草木之毒郁结熏蒸,遂成瘴疠。又岩洞溪壑间,其气如丝如缕,如雾如云,间之或香或酸,或如稬米饭之气,或有焦臭之味者,皆瘴地也。”
道光《上思州志》所载十分细致:“邕(州)去桂千余里,属介边之区,大都暑多寒少,晴则热,雨则寒。一日之中,气候倐易。至其深山密菁之间,虫蛇草木之毒郁结熏蒸,遂成瘴疠。又岩洞溪壑间,其气如丝如缕,如雾如云,间之或香或酸,或如稬米饭之气,或有焦臭之味者,皆瘴地也。” 这里观察到的“瘴气”不仅形状各异,而且气味多样,甚为奇特。从类似文献的描述来看,人们所观察到的“瘴”是一种毒气无疑。
这里观察到的“瘴气”不仅形状各异,而且气味多样,甚为奇特。从类似文献的描述来看,人们所观察到的“瘴”是一种毒气无疑。
其二是指“瘴病”,因瘴气所导致的疾病。隋代巢元方所著《重刊巢氏病源候论总论》分析了该病的地理位置以及症状与病因:“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嶂湿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疟。”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 明代李璆言:“岭南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此寒热之病所由作也。病者多上热下寒,既觉胸中虚烦郁闷。”
明代李璆言:“岭南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此寒热之病所由作也。病者多上热下寒,既觉胸中虚烦郁闷。” 清代俞震则认为:“瘴气为病,情形不一。非亲历其地者,莫能知也……瘴者,障也,天地自然之气,为崇山峻岭,障蔽不舒而然也。再加之以春夏之交,万物发生之际,乖戾郁遏……”
清代俞震则认为:“瘴气为病,情形不一。非亲历其地者,莫能知也……瘴者,障也,天地自然之气,为崇山峻岭,障蔽不舒而然也。再加之以春夏之交,万物发生之际,乖戾郁遏……” 俞氏所说的瘴气与瘴病似乎就不做区别了。
俞氏所说的瘴气与瘴病似乎就不做区别了。
从地理上说,瘴气似乎是一种南方、西南独有的自然现象,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下产生,而它又是瘴病致病的原因,因此“气”与“病”是紧密相连的。古人在记载时常常将之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混为一谈,因而“瘴”包含着两层意思。但很显然,不管是“气”或“病”都有极大的危害性。由于对瘴气的认识直接来源于对自然的观察,不需要专业性很强的中医病理学知识,而且也是了解瘴病的必要路径,因而首先引起关注。关于瘴气的成因,人们试图在地理上找原因,并对此进行十分详尽的分析,其中以岭南地区最为典型。通过这些论述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地理学的知识水平,而且也可洞悉国家知识阶层对南方边陲的总体印象,进而探讨形成这种印象的哲学基础。
古人有关瘴气的地理学解释以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最为详尽:
客有问余广右俗,冷热不以寒暑而以晴雨,即土人亦不得其说,但知此中阳气大泄,故多热而已,而不知其所以然,请以土薄水浅之云而申绎之。余曰:“此无他,特以地气有厚薄疏密之故也。广右地脉疏理,疏则阳气易于透露发泄,故自昔称炎方。一至天晴日出,则地气上蒸,如坐甑中,故虽隆冬亦无异于春夏之日。然其地居万山中,山皆拔起,纯是岩石,无寸土之附,石气本寒,今广右诸洞,深入里余,虽六月披裘,亦战栗不持,气寒故也。一至天欲雨,则石山输云,岚烟岫雾,踵趾相失,咸挟石气而升,幽寒逼人,故虽盛暑,亦无异于隆冬之时。及夫云收雨止,日出气蒸,乍热乍寒,无冬无暑,皆以是故。或谓南中同此土也。广右居交广之内,暖气反发泄过于彼土者何?盖他处山少,而广右纯山,山少者地土相兼,脉理本密,兼以地皆种植,尺寸不遗,地气上升,多宣泄于五谷。有粪壅浇溉,地面肥饶,故密而地气不甚泄。广右地气尽拔为山石,则余土皆虚,业已无石而疏理,又满眼荒芜,百里无人烟,十里无稼穑,土面不肥,谷气不分,地气无所发泄,安得不随日上升,而散中于人之肌肤也?以是知寒暑之故,半出于天,半出于地。风光日色之寒暑,出于天者也;气候之寒暑,出于地者也。地薄而疏理,则气升而多暑;地厚而理密,则气敛而多寒。非专为方隅南北之故也。向读《异域志》,见阴山沙漠之北万余里,有其地四时皆春,草木不凋者,曾疑其无有,极北愈寒,安得为是说也?乃今意诚有之,正为地各有厚薄疏密,其果不全系于天,与南北方隅之故也。若谓寒暑尽出于天,则今高山峻岭之上,渐近于天,渐远于地,宜其多暑而无寒矣,何故山愈高而愈寒,岂非土石厚而地气隔,故寒多?亦其一验。
清人程林就自己的理解进行了阐述:
瘴气乃山川毒厉之气,又云江山雾气多瘴,凡以其气郁蒸而然也。——且阳生于子,盛于巳;阴生于午,盛于亥;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长。而广南位当巳午,则阴阳之气蕴积于此可知矣。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阴也,土地高厚;东南阳也,地土卑下;而广南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所蕴积,是以四周之山,崇高相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不凋卒,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岐伯所谓南方地下水土弱,盖雾露之所聚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
程林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在解释瘴气形成时,特别强调南北地理、气候差异,试图说明瘴气是由于岭南特殊的地形、地貌所导致。然而古代中国地理学并未发展成独立科学的程度,所具有的思考常常与人们的“宇宙观”“文化观”交织在一起。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解释大致体现了中国传统“阴阳观”的内在思维逻辑。集哲学、医学于大成的《内经·素问》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所有的事务都处在“阴阳”的“力场”,不过只有“阴阳”互依、互济、协调,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即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所有的事务都处在“阴阳”的“力场”,不过只有“阴阳”互依、互济、协调,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即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如果“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如果“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根据这样的理解,岭南之所以会产生瘴气主要是由于“阴阳”失调,冷热不均。“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
,根据这样的理解,岭南之所以会产生瘴气主要是由于“阴阳”失调,冷热不均。“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 ,产生瘴气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观点之下,其实还隐含着一个更深刻的命题。
,产生瘴气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观点之下,其实还隐含着一个更深刻的命题。
相对于南方而言,中原又是何种景象呢?周朝时,大司徒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寻找“地中”,此处“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之后在西汉时的《盐铁论》中有进一步发挥:
。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之后在西汉时的《盐铁论》中有进一步发挥:
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
三国时期卢毓更将之具体化,他认为天地相交、阴阳相会的确切地点在冀州境内:“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 在这种阴阳平衡的地方,气候自然宜人。所以北宋晁补之指出:“中国,阴阳之中,土气和适。”
在这种阴阳平衡的地方,气候自然宜人。所以北宋晁补之指出:“中国,阴阳之中,土气和适。” 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也认为“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
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也认为“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 ,而“岭南之州,大抵多卑湿瘴疠,其风土杂夷,自昔与中原不类”
,而“岭南之州,大抵多卑湿瘴疠,其风土杂夷,自昔与中原不类” 。由此看来,因为“中国”处于天下之中心而获得独特的地理与气候的优势,较之瘴气横行的边陲如岭南者,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实有天壤之别。人们就这样将瘴与山水、树木、天气等联系起来,通过刻意渲染,造成岭南无处无瘴的印象。随着曾在岭南生活过的中原人的北返,这种观念不断强化,并传递给其他中原人,岭南作为瘴乡的恶名遂得以确立。经过这样的推衍,从而建构起地理关系的阶序性,无形中凸显了中心与边缘非对称的二元对立,同时也强化了中原人“文化优越感”的信心。在此种语境之下,对于瘴的分类就不见得客观了,还夹杂了许多臆断与想象。
。由此看来,因为“中国”处于天下之中心而获得独特的地理与气候的优势,较之瘴气横行的边陲如岭南者,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实有天壤之别。人们就这样将瘴与山水、树木、天气等联系起来,通过刻意渲染,造成岭南无处无瘴的印象。随着曾在岭南生活过的中原人的北返,这种观念不断强化,并传递给其他中原人,岭南作为瘴乡的恶名遂得以确立。经过这样的推衍,从而建构起地理关系的阶序性,无形中凸显了中心与边缘非对称的二元对立,同时也强化了中原人“文化优越感”的信心。在此种语境之下,对于瘴的分类就不见得客观了,还夹杂了许多臆断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