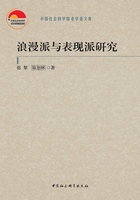
三 歌德与早期浪漫派
浪漫派对歌德的认识和态度,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变化最快最大的莫过于诺瓦利斯了。
起初,诺瓦利斯对歌德,特别是对他的《威廉·麦斯特》,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把歌德誉为“真正富有诗才的总督”“时代的头号物理学家”,他把《麦斯特》看作浪漫派小说的理想,并以这部小说为样板,动手写作《赛斯的学徒》。但是诺瓦利斯不久就后悔了,他发觉《麦斯特》是一部“矛头对准诗”的小说,是一部“糟糕和幼稚可笑的”书,“毫无诗意”可言,是“对诗和宗教等的讽刺”。诺瓦利斯并不满足于对《麦斯特》的批判,他还写了一部同《麦斯特》针锋相对的小说《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在他看来,歌德在《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里,让不和谐的和丑恶的现实战胜了诗,他诺瓦利斯则要以《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来拯救诗,为诗进行辩护。他的小说是“诗的神化”,赞美诗同宇宙、同自然、同生与死,同一切融为一体:世界变成了梦幻,梦幻变成世界。
弗·施莱格尔同歌德的关系不同于诺瓦利斯,始终没有出现急剧的变化和那种大起大落的态势,这是因为他对歌德和他的创作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他的不少评论颇为中肯,某些论著,如关于《威廉·麦斯特》的评论和《试论歌德早期和晚期作品的不同风格》,至今仍不失为文艺批评的杰作。他对歌德的赞颂,可谓语出惊人。在《论希腊诗研究》里,其中关于歌德的部分,发表于1796年,他称赞歌德的诗为“真正的艺术与完美无缺的美的曙光”,说歌德揭示了“美学教育的新阶段”。在发表于1798年《雅典娜神殿》上的《断片》里,他把法国革命、费希特的《科学论》和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并列为“时代最伟大的倾向”。
当然,弗·施莱格尔对歌德的赞颂并非毫无保留。他个人的笔记表明,他对歌德尚存某些疑虑,他对歌德的钦佩渐渐地在降温。他很早就察觉到《威廉·麦斯特》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它是“并非完全神秘的”。他甚至声称歌德的作品“很像无意义的艺术品”,“歌德的作品没有统一性、完整性,随便从哪里都可以开端”。[13]在奥·威·施莱格尔同歌德的关系中始终没有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他对歌德的钦佩被认为是真诚的。但他的热情末了还是冷却下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浪漫派同歌德的关系难免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但不管怎样,在互相的关系中,双方都是受惠者。歌德作为年轻一代景仰的人物,对浪漫派作家的成长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施莱格尔兄弟对歌德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18世纪20年代,歌德以他的《维特》在文坛上的确红极一时,但时过境迁,进入80年代,他差不多被人遗忘了。施莱格尔兄弟步入文坛时,他主要是以《维特》和《葛茨》的作者为人称道。施莱格尔兄弟对歌德的评论,使他的声誉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获得了恢复。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里指出:“尽管歌德装出一副高贵的神气,但他的声誉绝大部分得归功于施莱格尔兄弟。”[14]歌德晚年在追忆他同施莱格尔兄弟的关系时说:“洪堡和施莱格尔兄弟,都是在我的关照下崭露头角的,他们对我有难以述说的好处。”[15]
浪漫派的发展变化有个过程,歌德对它认识也有个过程。他对待浪漫派的态度,也先后经历过友好相处、等待观望和反感仇视这样的变化。
起初,歌德同施莱格尔兄弟颇为友好。他欢迎奥·威·施莱格尔去耶拿任职,在耶拿期间,两人过从甚密。弗·施莱格尔抵达耶拿后,他在日记里一再记下兄弟俩的名字,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颇为有意思的是,如上所述,弗·施莱格尔在世纪更迭前后,不顾自己的挚友诺瓦利斯对《麦斯特》的反感,为歌德这部小说大唱赞歌;而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歌德也置自己的密友席勒对施莱格尔兄弟的厌恶于不顾,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他甚至不理会席勒和观众的反感,在魏玛上演奥·威·施莱格尔的剧本《约恩》和弗·施莱格尔的《阿拉科斯》,以致席勒1802年6月抱怨说:“接待施莱格尔兄弟乃是他的病态。”但是歌德毕竟城府很深,老于世故,他人实难抓到他的话柄。1799年初,维兰德质问他,他怎能接受施莱格尔兄弟“如此恶心的”夸奖,歌德巧妙地答道:“我得听之任之啊,正如我遭他人放开喉咙谴责一样。”[16]
歌德之所以重视同施莱格尔兄弟的关系,不仅因为这两位学者年轻有为,善于理解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因为世纪更迭前后双方观点一致或接近,如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崇拜;对时代与社会的论断与批评(断定当今社会敌视诗,当今散文支配诗,理性支配感性,科学支配艺术);认定亚里士多德摹仿自然的基本原则业已过时,它只适于“朴素的”诗,而“伤感的”诗是要表现理想,反对平庸的说教文学的。
1800年以后,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等人的影响下,德国浪漫派迅速发展。浪漫派的“离经叛道”倾向引起歌德的警觉和不满。1824年3月24日,诗人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追忆说:“他和蒂克真诚相好,他很了解这位青年人的才能和卓越的贡献。然而施莱格尔兄弟崭露头角后,就觉得他威望太高,遂将蒂克作为一位人杰抬出来同他分庭抗礼,以保持一种均势,从而伤害了他与蒂克的友好关系。”[17]浪漫派开始走上“叛逆”道路后,歌德在不同场合,对它发出过警告。诗人1805年发表的《温克尔曼》一文,掀开了诗人发动的一场批判浪漫派斗争的序幕,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前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歌德同浪漫派的斗争,并非个人之间的摩擦或利害冲突,而是魏玛古典主义与浪漫派在文艺观点上的矛盾冲突。主要分歧在下列三个问题上。
一个问题是,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化,还是仰慕中世纪欧洲文化。的确,浪漫派作家起初对古希腊文化非常顶礼膜拜。弗·施莱格尔就非常赏识柏拉图、温克尔曼和希腊的悲剧作家。他把希腊文化看作一幅完美无缺的人类图景,把他们的文学誉为“自然诗的准则和典范”。难怪席勒称他为“古希腊狂”。但在世纪更迭之后,浪漫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810年,弗·施莱格尔在他的文学讲演中,把起初被他称赞的古希腊文学斥为“非基督教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提出把“基本上是古典时期的同基本上是近代的结合起来”(1894年2月27日致奥·威·施莱格尔的信)。现在,浪漫派作家把古典的和近代的都搁置一边,以便转向中世纪,转向但丁、卡蒙斯、塞万提斯、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和莎士比亚,转向中古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文学。因为从这些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文学中,他们能找到梦寐以求的基督骑士道德——荣誉、爱国主义、爱情、激情和战斗的勇敢,能找到他们所追求的诗的意境(Poetizität),而这种诗的意境在敌视艺术、诗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处于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浪漫派作家起初为之所倾倒的是美和娱乐一类概念,那么现在他们所醉心的则是内心、心灵、同情、痛苦和对永恒与无穷的渴望一类词汇。1806年,奥·威·施莱格尔在致富凯的一封信里,对浪漫派理论的转变作了这样的解释:“为什么我们感到浪漫主义的诗比古典的更内向和更神秘呢?”“因为希腊人只考虑欢乐的诗学,而痛苦比娱乐、严肃比轻浮更富有诗意。”浪漫派作家约瑟夫·格雷斯对中世纪的崇拜是十分引人注意的。他在《德意志民间话本》(1807)的序言里把中世纪美化为“近代欧洲历史的青年时代”“诗的新园地、浪漫派的伊甸园”。
歌德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一向推崇备至,把它奉为典范,看作国际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文化,歌德并不一概反对。浪漫派发掘、搜集和整理出版历代许多为人们所忽视的文化宝库,也博得歌德的赏识。歌德所反对的是浪漫派鼓吹的中世纪的基督教骑士传统。
歌德同浪漫派的另一个基本分歧是艺术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皈依天主教,艺术同宗教的勾结,一开始就是德国浪漫派的内在倾向。1793年,瓦肯罗德尔与蒂克一起赴纽伦堡作艺术与教育考察。瓦肯罗德尔记述这次考察的散文集《一个热爱艺术的修饰的内心倾诉》(1797年由蒂克发表),可以称作德国浪漫派最早的纲领性著作之一。年轻的浪漫派作家在文章或随笔中,表露了对文艺复兴艺术,特别是对丢勒等古代大师的由衷敬仰之情,他们把拉斐尔的绘画奉为使人沉思默想的宗教艺术典范,并以拉斐尔来攻击持古典主义看法的温克尔曼,声称最高的创造力源出于艺术与虔诚的结合。弗·施莱格尔也鼓吹宗教同艺术相结合(《1802—1804年间巴黎和荷兰绘画描写》,《对基督教艺术的见解》,1823),声称“艺术自身不消亡,就永远离不开同宗教的结合”。诺瓦利斯是双料的基督教卫道士,他不但有理论(《基督教或欧罗巴》,1799年作,1826年发表),而且有创作实践(《宗教》)。他声称:“诗人和牧师起初合二而一,后来才一分为二。真正的诗人总是牧师,正如真正的牧师总是诗人一样。难道将来不该再导致事情的旧有状况吗?”《教会同艺术家的联盟》是奥·威·施莱格尔的一首长诗,诗的名称足以表明作者的思想立场了。
歌德一贯坚持批判宗教神秘的思想倾向。对基督教的反感驱使他同一些有交情的朋友分道扬镳。18世纪80年代他同拉瓦特尔的决裂,就是因为这位瑞士朋友在其作品里宣扬基督教假仁假义的倾向。在90年代,施托尔贝格那宣扬基督教的《柏拉图谈话录精选》,也遭到了歌德的批判,从而促使歌德和席勒掀起德国文学史上那次著名的“讽刺短诗”之战。
浪漫派的宗教神秘倾向激起歌德的强烈不满。1805年发表的《温克尔曼》一文,可谓声讨浪漫派的一篇檄文。歌德称赞温克尔曼是不信奉宗教的,说他加入天主教,纯粹是形式,借以表达他对浪漫派皈依宗教的憎恶,他说:“若要评论温克尔曼那种所谓宗教变动,务必要看到他这种非基督教的思想方式,这是对基督教本性的疏远,甚至是对它的反感。”
世纪更迭之后,德国浪漫派在哲学、文学、造型艺术诸领域的影响,日甚一日,大有抵消以古希腊罗马为典范的古典美学作用之势。歌德从后期浪漫派的作用,看出了瓦肯罗德尔《内心倾诉》的消极影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817年,歌德毅然决然在其主编的《论艺术与古代》杂志上,发表其好友海因里希·迈尔的文章《新德意志宗教爱国艺术》,以此为重磅炸弹向浪漫派发动大反攻。这篇文章是在歌德启迪下产生的,体现了歌德的观点。文章以弗·施莱格尔和瓦肯罗德尔为靶子,尖锐地批判了浪漫派宗教神秘和蒙昧主义倾向。前者被称作古代宗教思潮的先驱,他在其主编的《欧罗巴》杂志上“充当了新的仿古的天主教——基督教艺术趣味的书面教员”[18];后者的《内心倾诉》充满了虔诚的艺术妙语和宗教艺术趣味,富有魅力,作者借此把热情伤感的青年人,吸引到艺术宗教(Kunstreligion)里来。在歌德看来,这种新的宗教艺术思潮,乃是“一种幻想的天真幼稚的宗教狂”,被它所吸引的人,证明自己是“半瓶醋知识和一知半解的一代青年”。[19]歌德预料到迈尔这篇文章,“将像一颗炸弹投进拿撒勒画派艺术家的圈子里”[20]。18年后,海涅在谈到这篇文章的作用时写道:“歌德仿佛用这篇文章在德国文坛上发动了他的雾月十八政变;他极为粗暴地把许雷格尔(即施莱格尔——笔者注)兄弟赶出庙堂,并把他俩的很多最热心的弟子争取过来,那些早已不能容忍许雷格尔督政府的群众,向他欢呼喝彩,这样歌德便在德国文坛上奠定了他的寡头统治。”[21]
歌德同浪漫派的第三个严重分歧是艺术同自然的关系问题。重主观,轻客观,本是浪漫主义的普遍特征。在浪漫主义故乡的德国,浪漫派这一特征尤显著。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丑恶的社会现实驱使诗人们逃避现实。作家艺术家对敌视艺术的社会很反感。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使人们深感失望。逃避现实,力图从主观精神世界中求得安慰,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点歌德也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时代都有一种客观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这一点你不仅在诗方面可以见出,就连在绘画和其他许多方面也可以见出。”[22]其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德国浪漫派发展的时代,正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盛行之时。两者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谢林的自然哲学成了浪漫派崇尚自然、喜欢描写自然美景、表现人与自然亲密无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那么费希特的“唯我论”则为浪漫派推崇无所约束的个性,为他们随心所欲的主观意识的专断提供了理论根据。费希特被看作人的主观性的发现者。他的“唯我论”否定“物自体”的客观存在,而以康德关于意识创造现象界、自然界这一论断为出发点,宣称“自我”(人的意识)为认识的主体,“非我”(客观世界)为“自我”的创造物,从而把康德的唯心主义推向顶峰。
应该指出,席勒的唯心主义美学对浪漫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康德在《批判力的批判》中从先验哲学上论证了美学趣味判断的自主性。席勒据此在艺术理论中发展了这种自主的设想。他认为文艺不应受任何政治目的和社会效果的制约。这种主张同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所强调的文艺的社会效果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自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席勒却认为艺术自主论并非否定启蒙运动,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它的理想。因为在席勒看来,艺术只有同社会的政治行动和推究哲理的理性并起并坐时才能从最广的意义上接受政治职能。[23]浪漫派理论接受了这种艺术自主的设想,主张发展想象力,把它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把这看作艺术的新职能。
浪漫派这种重主观幻想轻客观现实的主张,同歌德的理论自然是格格不入的。歌德推崇客观艺术,强调诗的根基在于外部现实,希望“给现实以诗的形态”。晚年,他还这样讲述诗同客观现实的关系:“只要他(诗人)仅仅表达他的一些主观感受,他还称不上诗人;但他一旦懂得把握并表达世界,他就是一位诗人。”[24]歌德之所以对古希腊罗马艺术推崇备至,就是因为古希腊罗马诗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紧紧抓住身边的东西,真正的东西,实在的东西,甚至就是他们的幻想也都是有血有肉的”[25]。
如果说古希腊罗马艺术始终是歌德心目中的典范,那么自然就是诗人仰慕的另一个样板了。对歌德来说,艺术与自然有着血肉般亲密的关系。自然知识构成了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他的自然科学著作成了他的艺术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来源。在如何看待艺术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歌德不但同浪漫派发生了严重的碰撞,而且同他的密友席勒也产生了分歧。对于席勒和浪漫派来说,既然社会现实丑恶,超越现实,与之保持距离是诗人的使命,那么亚里士多德关于摹仿自然的原则就理应是过时的创作方法了。而对歌德来说,艺术必须遵循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是古典的创作原则,必须坚持。当然,歌德的观点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早年,在狂飙突进时期,他固守艺术等于自然的原则。但在他的首次意大利之行以后,歌德看出艺术与自然情况各异,各具特性,需要加以区别。他在《神殿前廊入门》(Einleitung in die Propyläen)一文中还承认,“自然同艺术之间有一道鸿沟”。尽管如此,歌德仍然认为摹仿自然是接近现实的一个最初阶段,艺术是受到它的制约的。
歌德通过他的意大利之行,看清了古人是如何处理艺术同自然的关系的。在意大利,他目睹了古人的伟大作品,发现它们达到了艺术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在《意大利游记》(1787年9月6日)中,联系到荷马的创作,歌德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些水平高超的艺术品,都是遵循真正的和自然的规律创作出来的忠于自然的作品(Naturwerke)。任何随心所欲的,想象出来的都行不通。这就是必然性,这就是上帝。”寥寥数语概括了歌德早期古典主义的艺术主张。按照诗人的主张,伟大的艺术品的创作,务必“遵循真正的和自然的规律”。这是诗人考察了古人艺术实践后得出的经验。不言而喻,这里的所谓“真正的和自然的规律”,同诗人一贯强调的艺术“要忠于自然,要恭顺地摹仿自然”,是一脉相承的。对于主观随意性,诗人一贯持批判态度,他把“纯粹的主观性看作为现时代的病态”[26]。
歌德并不一概反对幻想和虚构。恰恰相反,他认为在艺术创作中,虚构是必要的:“……在艺术创造的较高境界里,一幅画要真正是一幅画,艺术家就可以挥洒自如,可以求助于虚构……”[27]
晚年,歌德对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做了明确的概括:“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28]这段精辟的论述告诉我们,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艺术家既然是自然的奴隶,那就“要忠于自然”,“要恭顺地摹仿自然”,从而排除了创作中的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他又是“自然的主宰”,那就可以使自然屈从于个人的意志,借助虚构,使幻想同自然(现实)、理想同现实、主观同客观达到完美的一致。
在歌德看来,艺术家同自然的这种双重关系,乃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法则。艺术家只有尊重这种关系,遵循这一法则才能创造出高水平的作品来。而浪漫派崇尚主观随意性,这势必把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变成了单一的主仆关系:前者成了可以滥施淫威的主人,后者是前者随便使唤的婢女。这种单一的关系,势必把艺术引入歧途,因而遭到歌德的激烈反对。
随着一些浪漫派作家政治思想和文艺观点上的倒退,歌德对浪漫派的反感也愈来愈强烈,以至晚年说出了“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这句名言。这绝非歌德老人偶然失言或感情冲动所致。除同爱克曼的谈话(1829年4月2日)外,在《格言与感想》中在谈到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创作方法时,[29]诗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说“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呢?诗人的唯一标准是自然、客观、现实、真实。在歌德看来,这些词的词义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如上所述,歌德之所以把古希腊罗马人奉为典范,正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抓住身边的东西,真正的东西,实在的东西,甚至就是他们的幻想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浪漫的”之所以是“病态的”,主要是因为浪漫派推崇主观随意性,从而违背了“自然、客观、现实、真实”的标准。歌德把主观性或纯粹的主观性称为现代的通病或现时代的疾病。1808年8月28日他在同里默尔的谈话中把不真实的和不可能的同pathologisch(病态的)和浪漫的等量齐观。[30]霍夫曼的《金瓶》(惯译《金罐》)是一部充满幻想的艺术童话。歌德在日记里这样记下他的读后感:“着手读《金杯》(指《金瓶》),感到不舒服,我诅咒金色的小蛇。”此事多少说明歌德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在歌德看来,主观性、不自然、不现实、不真实都是同义词或近义词,又都是“病态”的征兆。
歌德无疑是位伟大的思想家,对问题的观察敏锐、深邃,对文艺问题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他关于“浪漫的是病态的”这个论断,实不敢苟同,理由有三。
其一,把“浪漫的”笼而统之称为“病态的”,实有主观武断之嫌。倘若“浪漫的”是指流派而言,确切地说,如果仅指德国浪漫派,持论也似欠公允。不可否认,浪漫派有不少不健康的因素(诸如宗教神秘倾向),理应受到批判。浪漫派的成分毕竟很复杂,绝不能说所有浪漫派作家都沉湎于幻想,都是脱离现实的,因而都是“病态的”。众所周知,德国浪漫派本身是个派中有派的文艺流派,其成员的思想倾向、文艺观点、作品风格并非“清一色”。譬如,海涅把诺瓦利斯同E.T.A.霍夫曼对比时就指出:“诺瓦利斯连同他笔下的那些虚幻的人物,一直飘浮在蓝色的太空之中,而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31]而如果“浪漫的”是指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那简直是“横扫一切”了。尽人皆知,浪漫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源远流长。古往今来,世上不知有多少作家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歌德本人把自己摆到古典主义一边,他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浪漫主义大家族的一员(席勒也称他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不自觉地进入了被他“横扫”的事物之列。他的这一论断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其二,根据现实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人们今天正重新审视文艺领域中主观幻想的内涵。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出发,主观幻想与文艺的真实性并非毫无缘分。在近年来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探索中,前民主德国一些著名作家指出,应该拓宽“现实”与“真实”的含义。在安娜·西格斯看来,现实不仅仅是独立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不仅仅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事物,而且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幻想、愿望;作品在反映生活真实时也应表现“幻想真实”,表现人的主观世界。克里斯塔·沃尔夫认为,主观真实(或内心真实)是比外部真实更加本质的真实,因此只有在反映外部真实的同时着力表现内心真实,才能完整而又深刻地反映现实。
其三,歌德的所谓“浪漫的”是“病态的”论断,不利于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歌德在文坛上至高无上的权威赋予他的论断以极大的威力。毫无疑问,他的论断给浪漫派以沉重的打击。它成了后代批判乃至全盘否定浪漫派的重要依据。德国浪漫派作为德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留下了极为丰富宝贵的遗产,只有对它做出公正的评价,才有利于批判继承这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