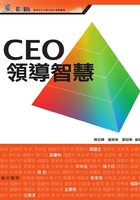
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以下談談我們的旅程。艾默生是一家環球企業,在不同地域發展時,我們很注重四方面的投資——營銷、研發、生產和出口採購。我們最重視的策略是:在投身任何大型投資前,先得確保投資的成果在日後有一定市場。
我們在中國是怎樣開始的呢?那時是1978年。我們就像哥倫布,並不知道前路如何,也不知道應採取甚麼策略。一開始我們並沒有甚麼鴻圖大略,套用鄧小平先生的名言,我們是“摸着石頭過河”。我們不知道應怎樣過河,只是步步為營,踏上一塊石頭,若是穩固的,便踩上去,然後又展開第二步。我們就是這樣開始的。我們心中只有一個簡單信念:中國市場是不容錯過的。
艾默生採用了一套“推拉策略”(push—and—pull strategy)。“推”是我們的主席和高層領導,推動營運部門,要求他們一定要去中國,當然也給予了下屬適當的賞罰。“拉”是指我這類人,身在中國或在中國附近,嘗試提供比較良好的營運環境,令各子公司較容易進入中國發展。
實際上是怎樣做?我們要得到政府批准,要確保當地有水──看起來很簡單,是嗎?但那是必須的。我們也要確保當地有電、有煤氣、有公路、下雨時不會有水災⋯⋯其實並不是這麼容易的。
我們最初規模不大,並不斷從錯誤中學習,以繼續前進。我們在1978年,即文革後開始這趟旅程。那時中國剛開放。我是在1986年加入艾默生的,是中途加入這趟旅程。在1990年末,我們在中國的銷售額約為七千萬美元。1990至2000年是這趟旅程的第二階段,我們的銷售額增加至三億四千萬美元,升幅非常可觀。但升幅最大的還是旅程的第三階段──2000年以後。
我們怎樣達至這個佳績?早在1978年,外地公司不能直接在中國設廠,所以我們要從其他國家出口,透過出入口公司把產品售予中國。第二階段是技術轉移,那時中國還未完全開放,中國政府跟我們說:艾默生,你的產品和技術都很好,我們很喜歡,但我們更希望你把技術轉移給我們,讓中國可以自行生產這些產品。我們給你合約,但合約完結後請讓我們自行運作。
接着我們在北京成立了代表辦事處,加強業務推廣。以上所講的平台都進展緩慢,並沒有帶來顯著的業績。下一步是成立沒控股權的合資企業。這時中國正逐漸開放,我們便把握時機。接下來是成立有控股權的合資企業,於是我們可以直接管理,可以培訓自己的員工,可以自行招聘,可以引入我們的企業文化。
下一部分更重要。我們決定作更多直接投資,希望在亞洲大展拳腳。公司在亞洲派駐了兩位重要人物──Bob Staley與Dave Farr。事實上,香港是艾默生亞洲之旅的重要一站。Staley是當時公司的副主席,他決定留駐香港,以加快在中國作投資的決策過程。過往我向美國總部同事推銷我的理念,聽的人很多,但卻沒有行動。要說服他們很困難,他們一邊點頭說:“Peter(任錦漢),我同意,這值得做。”但卻沒有行動。為改善這情況,我們的管理層決定在亞洲派駐一些非常高級的行政人員。我想,當時我們是唯一一家Fortune 500企業,在亞洲派駐公司的第二號人物(即副主席),讓他在這裏生活、了解、分析和處理這裏的各樣問題。當然,這也方便了我,我只要把我的理念告訴他,其餘的交給他便可以了,他會說服美國的同事,並且從速投資。
Dave Farr也是美國總部派來香港的,他是年輕的副總裁,來負責管理艾默生其中一個業務部門,包括在中國的業務。想不到七年之後,他成為我們全球業務的CEO及主席。
艾默生在2000至2005年間業績顯著飛升,我們究竟做了甚麼?企業併購。儘管明知文化差異大,管理上可能出現問題,但我們還是大膽收購中國公司,只有這樣才能在中國大放異彩。
其中一項主要併購是在2001年,買入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屬下的一家子公司,作價七億五千萬美元。人人都說我們瘋了,竟花這麼多錢去買一家中國企業。但幾年下來證明那收購是值得的,我們的銷售額大幅攀升了。
我們現在在中國有34家公司,大部分是生產廠房,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我們不是有意計劃成這樣,那是自然而然的發展──當機會來到,我們便把握。我們在中國還有11個研發中心。事實上我們的中國公司已持有350多項專利,全部都是在中國研發的。我們在內地繼續從事四方面的重點投資:研發、生產、營銷和出口,這巨輪會繼續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