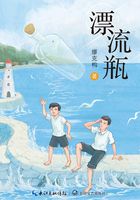
第3章 宴席
反正,就是这一天吧,我听到了温州鼓词,被牛筋琴的声音吸引,为它迷醉了。
反正,也就是这一天吧,我第一次见到了少年茂科,一个瘦长、羞涩而洁净的少年。
我的身世从此改变了。
少年茂科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开始。
没错,银鸥她们的家就是我的新家。我要到她们家当儿子,她们家缺少一个男孩。
我终于明白了,她们姐妹五个为什么在春寒料峭的中午到两个村庄交界的苦楝树下捡果子,她们是要迎接一个陌生的弟弟或哥哥到自己的家中。对她们而言,我令人好奇,令人期盼,又令人不知所措。作为一个陌生的闯入者,我的角色似乎自迈入她们家门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很重要,意味着香火繁衍;又是“侵入者”,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结构,破坏了原来的生活秩序。一切要重新调整了,包括房间和食物的分配。更离奇的事情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家中的三姑娘,也就是那个理着寸头的叫“状元”的女孩,家中原来是当男孩子养的,将来要许配给我。也就是说,长大后我们要成为一对儿,结婚生子。这个安排是多么精心而巧妙,又是多么用心良苦啊,我们真正亲如一家了,我甭想离开这个家庭了。
银鸥背着最小的妹妹,姑父带着我,银娣、状元、及弟几个跟在后面,一行人可谓浩浩荡荡,向我未知的家走去。离盐廒越近,围观的人就越多,尾随的人也越多。秘密似乎已众所周知:吴家要来一个儿子,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婿吧,是同村的劁猪匠和接生婆的外甥,母亲不在了,父亲也不知所终。
人们对我指指点点,嘴巴里发出“啧啧啧”的声音,不知道是称赞还是叹息。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似乎都来了,一进村口,跟随在后头的“尾巴”一下子就长出来很多。有几个连走路都不稳当的孩子因为跌跤而在后面大哭起来。我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无限担忧起来。
姑父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安慰我:
“快到家了,不怕。”
到了一排房屋前,最早迎出来的是姑妈,她是一个洁净而微胖的中年妇女。忙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她,她走路、挥手、说话,都显得匆匆忙忙:
“阿添来啦。这就好,这就好。快走,我带你一起去,我带你一起去。”
经她这么一催,时间似乎也过得快了起来,脚下的路也缩短了。反正那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一下子被拉开了好几步远。
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一阵硝烟轻轻腾空而起,弥散开来。放鞭炮的这户人家,新粉刷的墙面在一大排房屋里显得特别耀眼。屋前也围着好些人,看到走来的我们,人们的脸上马上堆起了笑容。一个瘦瘦的高个子女人笑着向我走来,脸上的皱纹因笑容而一道道叠起来,露出大嘴巴里一口整齐的牙齿。她的笑真诚而又为难,似乎有讨好的成分,又心有不甘。她的头上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头巾,在乡村只有坐月子的人才会有这副打扮,而这副打扮让我更加恍惚。我疑惑地看着刚刚相认的姑妈,不知所措。姑妈的言语依旧匆匆忙忙,她告诉我:
“叫婶,以后就叫婶了。”
我张大了嘴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叔是后面那位,也要叫。叫叔,叫叔。”姑妈说。
我还是什么也叫不出来。也许我叫了,但声音轻得连我自己都听不到。
“没事,没事,先吃饭,先吃饭。”高个子女人说。
“大家都坐下来,都吃饭,不要客气哩。”后面那位壮实的男人说。他就是我姑妈指的“叔”。我觉得他长得很精神,浑身很有力气的样子,完全不像“婶”,一副枯瘦的模样。
闹哄哄的人群慢慢散开来,分散到几间屋子里。原来,饭桌都已摆好。我被领到一张几个大人已经就坐的桌子旁坐下,姑父和他们正说着话。桌上已经放了几个冷盆,分别是虾干、鳗鱼鲞、银蚶、鱼饼、猪油渣、油炸菜丸子、盆菜生、腌菜梗。这还是一个刚刚能吃饱饭的年头,不是家中办大事,哪里见过这样的排场!
食物的诱惑力很快超过了一个陌生的来客。大家倒上酱油、醋或者虾酱作为调料,开始剥着虾干和银蚶,或者夹起鱼饼、鳗鱼鲞和油炸菜丸子吃了起来。很快,上来一盆热气腾腾的猪肉炖萝卜,香气飘了过来,我已顾不上什么陌生和惊慌,眼睛就被这一盆猪肉勾住了,嘴里直咽口水。我根本没记住桌上的这个大舅、那个二舅,恨不得嘴里伸出一只爪子,抓住香喷喷、油光光的猪肉统统往嘴里塞。我的馋相肯定难看极了,好在也没有人盯着我,他们——包括大舅、二舅、叔和姑父,都争先恐后地抓起筷子夹肉,埋头大嚼起来。我的碗里被放进了一块大肉。“谢天谢地!叔,你就是我的亲爹!”我心里说,“有肉吃,我就留在你们家了,给你当儿子了!”
待我一块肉吃完,大盆里已空空如也。
“这口猪去年年关都没舍得杀,现在算派上用场啦!”好像是大舅的话。他接过叔递给他的一支“瓯江牌”香烟,笑眯眯地看着大家说。
“家里又抓了猪仔,割猪草的事儿,以后就交给你啦!”叔忙着给人发香烟,接过话茬,看了我一眼说。
话音刚落,一盆带鱼烧盆菜端上来了。新鲜的带鱼还闪着银色的鳞光,切成一段一段的,都是两指宽,肉质洁白,富有弹性。在靠海的村庄,带鱼啊、黄鱼啊、墨鱼啊,都不是什么稀罕货,我在新美洲的林子里生活的时候,赶海的人路过小木屋,进来喝口水,就会随便留下几条给我们。盆菜也不稀罕,它是萝卜的一种,只是长成了盆子的形状,但跟白萝卜比有一丝甜味,切成块状的,和带鱼放在一起烧是绝配,带鱼的鲜味会渗入盆菜之中,而盆菜苦中带甜的味道恰到好处地去除了带鱼的腥气。如果上面再撒上几根细芹,算得上是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盆菜只有过年前后那几个月才有,平常地里长不出来;也只有江南平原这一带才有,别的地方是很少见到的。这么一想,其实也算是稀罕之物了。
又是一阵哧溜哧溜的声响,一盘带鱼炒盆菜便瓜分殆尽。
然后上来一盘韭菜炒鸡蛋。韭菜碧绿,鸡蛋焦黄。其实也没多少鸡蛋,只有几片零星地点缀着。韭菜是满满的一盘,它在乡村实在是不宝贝的常见物,割掉了一茬又长一茬。见了春风就长的,除了春草,就数它了。但它比春草有精神,从不胡乱生长,它也有小麦幼时的可爱,不仔细分辨,倒是分不太清楚的。大家的筷子就翻拱着这盆菜,争相挑走了仅有的一点点炒鸡蛋,留下韭菜像鸡窝似的散乱着。
上来一盆蒸黄三。在靠海的乡村,因为长得极像,黄三被称为黄鱼的兄弟。黄鱼有七兄弟,除了大黄鱼、小黄鱼,还有黄姑鱼、梅童鱼、鱼、黄唇鱼、毛鲿鱼。黄姑鱼排在大黄鱼、小黄鱼之后,位列老三,俗称黄三,名字真是十分形象。它比黄鱼长得粗壮,鳞片的金黄颜色比黄鱼浅,肉质也比黄鱼粗。这个年代,黄鱼也不算稀罕,黄三更算不上什么了。
又有煮花菜、炒卷心菜等几盆蔬菜上来,最后是一大盆的米饭、一大碗鱼味汤。
鱼味汤也好着呢,里头的鱼丸是刮了鱼的肉,搅拌了面粉,用拳头一团团捏着,从虎口冒出来,用调羹一个个摘下来,直接就入了铁锅里滚烫的汤水中,要加醋,也要撒胡椒粉,然后用葱花点一点,吃起来十分开胃。
大人们喝着土烧酒。他们的话渐渐多了起来,嗓门也渐渐大了起来,讨论起当年生产队分田到户到底公平不公平的事情来。
一碗白米饭下肚,我的肚子滚圆滚圆的。唉,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这么热闹的场景也是头一回见到。如果这就是姑父说的“好日子”,我倒是巴望不得的。至于割猪草、养猪什么的,不过小事一桩。让人难以割舍的,倒是我在海边的小木屋了。啊,我想起来了,还有好多漂流瓶在床底下,现在,到底有多少个了?弹涂鱼、招潮蟹、缠绕在正梁上的“菜花王”蛇怎么样了?不不,哪有好多个漂流瓶,分明只有一个漂流瓶,我已经随身带着了。
“茂科来啦!唱词人来啦!”门口突然喧闹起来。亲戚家的孩子们纷纷从桌上下来,围住了一老一少两个走街串巷的鼓词艺人。“茂科,茂科!”他们对少年更是叫个不停。我趁机滑下桌,跑到门口去看。一老一少已经坐了下来。老人是个盲人,矮小且瘦弱,不停地翻动着眼睛里的白翳,少年则白净而细长,正为老人摆开牛筋琴、扁鼓。老人摸索着从布袋中掏出一副三粒板,清了清嗓子,打了几个节拍。随后,他又摸出一根小棒槌,在牛筋琴、扁鼓上一阵敲打,声音甚是悦耳。
“主人家和诸位人客,刚刚晓得好事,连忙赶来。春和景明喜事降,吴家香火传千年。我今儿个给大家唱一曲《宝莲灯》。唱得好,给碗饭吃,蒸条鱼来,再赏上一斗米;唱得不好,赏个馍吃,给碗汤喝,舀一碗番薯丝。”老人说。
“盲瞠人,这会儿才来,肉都吃完了。”叔从里头出来,说道,“要不是茂科带着来,你这就得打道回府。”
被称作“茂科”的少年羞涩地搓了搓手,红着脸笑了起来。
“唱词哩,唱词哩!”喝了土烧酒的大人们在屋里喊,“把最好听的唱上来!”
老人端坐好身子,左手打着三粒板,右手轮流敲着牛筋琴和扁鼓。一段冗长的序曲过后,他用浑厚的嗓音唱道:
西岳华山接苍穹,
白云深处有仙宫。
仙宫琼楼连翠阁,
洞府芝兰伴青松。
洞府内,有一个,
华山圣母叫杨花萼,
二郎神是她亲胞兄。
她身边,有一个灵芝小婢女,
与圣母情投意合如姐妹。
今日是——
圣母嬉游到瑶池,
灵芝使女后跟从。
但只见,
蜂飞蝶舞花似锦,
万紫千红春意浓。
……
“唱得好啊!老师伯今天卖力气。两条黄鱼给你们蒸起来,白米饭给你们端上来。”叔的脸酡红一片,他兴致高昂地夸奖起唱词人来。
春日午后的阳光照在一老一少两个迎着太阳端坐的唱词人身上,我看到他们喉结滚动,直咽口水。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唱词人多为盲人,他们沿着各个村庄走动,说卖艺也好,说行乞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能够有口饭吃。由于他们行走不便,往往要找一个少年引路。那些贫穷人家的孩子,就有一两个人被父母送去做差,口食自然是不愁了,遇上有好年景,往往也能分点米面和番薯丝,改变一下家中的窘境。盲瞠唱词人一手搭着引路少年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他们沿着小河边的石板路走来的时候,笃笃笃的拐杖落地的声音远远就会传来。
在乡村,盲瞠唱词人算得上是消息灵通的人士,不用说哪个村庄演社戏、办集市这样的大事,就连任何一件红白喜事,包括孩子满月酒、对周酒(周岁酒),哪家娶亲、嫁女、做寿,上了年岁的老人去世,他们都会闻风而来。好客和殷实的人家,一见他们到来,就会客客气气地搬出条凳请他们坐下,让他们唱上一曲《精忠报国》《鸿门宴》《封神榜》等等。然后,等他们唱完后端上饭菜,让他们饱餐一顿。最后,再往他们的布袋子里倒入一斗半斗的大米。当然,有时吃闭门羹也是少不了的,大狗汪汪一叫,就能让人心里明白几分。
没有红白喜事的时候,他们也会到处走动,到那些大家族和爱听词的人家屋前立定,问一声:
“老师伯,今天有兴致听词吗?”
应了,他们就坐下来。没有回应或者被一口拒绝,他们就往下一家走去。
反正,就在这一天,我到了吴家做儿子。说是做上门小女婿,也许更准确吧。
反正,就是这一天吧,我听到了温州鼓词,被牛筋琴的声音吸引,为它迷醉了。
反正,也就是这一天吧,我第一次见到了少年茂科,一个瘦长、羞涩而洁净的少年。
我的身世从此改变了。
少年茂科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