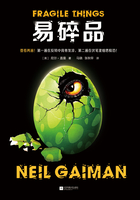
第2章 导言
“我想……回想这一生时,我宁愿发现自己迷恋易碎之物、虚度光阴,也不愿兢兢业业、终生力求道德完善。”有一天我在梦中想到这句话,起床后马上提笔记下。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此言针对何人而发,究竟有何含义。
大约八年之前,我策划这本幻想故事集时,本想管它叫《人们应该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有我们存在》。这句话来自一期周日版《小尼莫》(Little Nemo)[1]漫画,出现在某一格上的对话气泡里。今天,在阿特·斯皮尔曼(Art Spiegelman)的《无塔之影》(In the Shadow of No Towers)一书中,可以看到这一页的漂亮重绘彩图。原计划中,每个故事各借一位叙述者之口道出,他们极尽闪烁其词,玩弄花巧之能事,分头自我介绍,讲述各自的生活。读者会发现,他们都曾身处这大千世界,与我们同在。十多个人,十多个故事。本来是这么打算的,可是真正动笔时,这点子就毁了。我最后写出的,就是你在本书中看到的故事。故事该怎么说,写出来就成了什么样。有的的确还是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一段时间之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其他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的故事铺陈必须跨越数月乃至数年,否则怎么写也无法成形;有的故事在细节上有时间交叉之处,必须用第三人称叙述……
最后,书中所需材料终于备齐。我又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才好。原来那句话显然不再合用。就在这时,我听了戒零乐队(One Ring Zero)的《慧如我族》(As Smart as We Are)专辑,发现歌词中有我梦中所得之句。我开始琢磨:想到“易碎之物”时,我究竟想指代什么?
《易碎品》,拿来做短篇集题名倒也不错,毕竟易碎的事物实在太多。人易碎,梦易碎,心易碎。
绿字的研究
吾友迈克尔·里夫(Michael Reaves)和约翰·派兰(John Pelan)一起编辑文选《贝克街暗影》(Shadows over Baker Street)时,我为他写了这个故事。迈克尔给我的要求是:“我要你写个故事,把夏洛克·福尔摩斯扔到H.P.洛夫克拉夫特的世界里去。”我虽然嘴上答应,心里却觉得这设定很没谱:夏洛克·福尔摩斯身处纯理性世界,以解决问题为第一要务,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却蕴含极强的非理性成分,只有将未知事物封存在神秘之中,书中人才不至发狂。要是必须把两种元素结合起来,说故事的方法也必须有趣,以保证洛夫克拉夫特与柯南·道尔爵士的设计相得益彰。
菲利普·约西·法默(Philip Jose Farmer)的《沃德纽顿》系列(Wold Newton)[2]是我钟爱的童年读物。故事里许多虚构人物都被作者纳入同一世界背景之中。后来,我的朋友金·纽曼(Kim Newman)和阿兰·摩尔(Alan Moore)开始创作自己的《沃德纽顿》,在《安诺·德古拉》(Anno Dracula)系列与《非凡绅士联盟》(The League of Extraordinary Gentlemen)中着手融合世界。这些都让我乐在其中。看起来还不错,我想,也许这样的事我也能干。
故事原材料收集好了,最后所得成品比我动笔时的预期更为出色。(要知道,写作很像烹饪。有时候,任你花样百出,烤箱里的蛋糕就是不像样,但烤上一阵子,你会发现它越来越美味,好吃得出人意料。)
2004年8月,《绿字的研究》获雨果奖最佳短篇故事奖。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我的骄傲。一年之后,因为这篇故事,我更是神奇地成为“贝克街小分队”[3]中的一员。
仙舞
其实不大像首诗。不过大声念出来吧,很好玩的。
椅中的十月
彼得·斯卓布(Peter Straub)出任客座编辑,编纂《关联》(Conjunctions)选刊时,我给他写了这个短篇。其实几年前我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城开会时就开始动笔了。当时哈兰·艾里森(Harlan Ellison)让我和他合写一个短篇。我们坐在绳桩隔离区里,哈兰拿打字机,我抱着笔记本。哈兰动笔前还有个序言要写。所以我先写了一段开头,等他写完再拿给他看。“不对头,这开头太‘盖曼’了。”他如此评论道。(于是我把开头扔到一边,重开了一个故事,直到今天,哈兰和我还在继续写。诡异的是,我们碰头动笔时,总能把文章改得更短。)就这样,我硬盘上一直留着那个开头。几年前,彼得邀我加盟《关联》。我正好想写个关于鬼孩子和普通孩子的故事,算是为一本即将动工的长篇童书做个练笔。(长篇名叫《坟场之书》,眼下我正在写。)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构思出个大概,完工时,我把这篇献给雷·布拉德伯里,聊表敬意。同一个故事,若换他来写,一定比我强得多。
本篇曾获2003年轨迹奖最佳短篇故事奖。
秘屋
有两位南希,一位姓奇帕特里克(Kilpatrick),一位姓霍德(Holder)。她们编辑文选《局外人》(Outsiders)时向我约稿,要我写个“哥特式”故事。在我看来,所有故事中最“哥特”的当数《蓝胡子》(及其各个变种)。所以呢,我就写了首蓝胡子式小诗,故事地点就设定在当时我住的屋子里。那房子里没什么东西,几近全空。顺便一提,文中“烦忧”一词,诚如蛋头矮人在《爱丽丝镜中奇遇》中对爱丽丝所说,得算个“混合词”,占据了“烦恼”与“忧愁”之间的领地。
凶夜厄榭无面家仆禁脔烈欲记
想当年,我坐在东克罗伊登车站五、六站台之间,冒着冬夜的寒风,手拿铅笔涂着这个故事。那时我二十二岁,就快二十三了。写完以后,我把它打成铅字,给我认识的几个编辑看。有一位嗤之以鼻,直接跟我说他不喜欢这调调,而且真心觉得其他人也不会识这种货。还有一位,退稿之后一脸悲天悯人地解释道,这玩意儿油腔滑调,胡言乱语,永远不会发表。于是我把它扔到一边,好生暗自庆幸:如果真让广大读者看到这劣作,广招一番厌弃,这人岂不就丢大了?
就这样,可怜的故事无人再读,从文件夹移进纸盒,从纸盒里移进木箱,从办公室拿回地窖,最后又扔进阁楼。二十年间,我每次想起它,只会为当年的退稿而欣慰。直到有一天,一本叫《哥特!》(Gothic!)的集子找我约稿,我才想起阁楼里的手稿,让它重见天日,想看看能不能从中挽回些许剩余价值。
我开始读《凶夜厄榭无面家仆禁脔烈欲记》,看着看着,不禁微笑。真的,我发现,它非常好玩,非常聪明,是篇不错的小故事。其中固然有笨拙之处,但都容易修正。即使是文坛老手,这些拙笔也在所难免。二十年后的我拿出电脑,重写了故事,精简了标题,就寄了出去。虽然曾有专业人士指责它“油腔滑调,胡言乱语”,但看来那不过是少数意见。《凶夜厄榭无面家仆禁脔烈欲记》被许多最佳故事年选收录,还获2005年轨迹奖最佳短篇故事奖。
我也不清楚上面这段经历寓意何在。有时候,你只是没找对读者。同一件东西,不可能对所有人胃口。现在我经常琢磨着,不知道阁楼那些旧纸箱里还能翻出什么来。
大家都爱好孩子、记忆小径拾零
第一个故事灵感来自一尊莉萨·斯奈灵·克拉克(Lisa Snellings Clark)的低音提琴师雕像。我小时候就学过这种乐器。第二篇则是为一本“生活中的鬼故事”选集写的。集子中大部分作者写得都比我强,不过,我这篇虽不甚高明,却贵在字字属实。这两个故事最初收录于2002年新英格兰科幻协会出版社的《梦界冒险》杂集(Adventures in the Dream Trade),集子里多是简介、随笔之类的杂文。
打烊时分
迈克尔·沙邦(Michael Chabon)当年编过一本类型小说集,一来是为展示故事之中种种乐趣,二来也是为826瓦伦西亚募集资金。(826瓦伦西亚是一个专门培养少儿写作能力的社会活动组织。)集子名叫《麦克斯维尼惊悚故事大全》(McSweeney's Mammoth Treasury of Thrilling Tales)。迈克尔让我贡献一个短篇。我问他手头还缺什么类型的故事。他说,他想要个M.R.詹姆士[4]式鬼故事。
于是我就开始写鬼故事。不过,最终成品深受罗伯特·艾克曼(Robert Aickman)影响,有我喜爱的“怪谈”系列(“Strange Stories”)风格,倒不很像詹姆士了。(另外,我这篇以俱乐部为背景,也算个俱乐部类型故事,买一送一,实在实惠无比,童叟无欺。)这个短篇收录在几本最佳故事年选里,并获2004年轨迹奖最佳短篇故事奖。故事里所有场景都是真的,虽然名称略有改动。比方说,第欧根尼俱乐部其实叫特洛伊俱乐部(Troy Club),在汉威街(Hanway Street)。我也写到不少真人真事,真实程度超乎你们想象。当年我一边写,一边琢磨,不知那间小玩具屋还在不在,不知有没有人推了它,在它盘踞过的空地上重盖新房。不过,老实说,我一点也不想亲自回去一探究竟。
隐于野
英文中wodwo(或wodwose)这个词,意思是“林间的野人”[5]。本篇是为特里·温丁(Terri Windling)和埃伦·戴洛(Ellen Datlow)的《绿人》选集(The Green Man)写的。
苦磨咖啡
2002年我一共写了四个短篇。虽然这篇一个奖也没拿过,但我觉得,四篇作品里数它最好。这是为吾友纳罗·霍普金森(Nalo Hopkinson)的《魔符:神奇故事》(Mojo:Conjure Stories)选集写的。
他人
这是个莫比乌斯环式故事,也不知何时何处来的灵感。我只记得提笔记下点子,写出第一行,心里直犯嘀咕,也不知道这套路是不是已经有人用过。难道我童年看的弗莱德里克·布朗(Fredric Brown)和亨利·卡特纳(Henry Kuttner)作品里有这么一篇?总觉这种故事早有先例。点子简单精巧,完善而不失犀利,反而叫我心生疑窦。
过了一年左右,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待得无聊了,翻笔记时又看到这两行字。一把手头杂志看完,我就开始往下写。飞机还没着陆就大功告成。然后,我打电话找到好几个见识多广的朋友,把故事念给他们听,问他们是否觉着耳熟。大家都说没印象。平时都是有人先约稿我才写短篇,这次可没有编辑等着。我把它发给《奇幻、科幻杂志》的戈登·范·盖尔德(Gordon Van Gelder)。他收了这篇稿子,还重新起了个名。我倒也没意见。(本来我自己的标题叫“死后”。)
我经常在飞机上写作。刚开始写《美国众神》时,我在飞去纽约的路上写了个小短篇,觉得总能安进书里去。可后来不管我给它安排在哪儿,故事自个儿总不乐意。最后,书写完了,它还是无处容身。我把它写在圣诞卡上寄出去,从此忘得一干二净。几年过去,希尔氏出版社(Hill House Press)把它印在他们的圣诞卡上,分送给订户。(这家出版社也为我的书出过非常非常精美的限量版。)
这个无处容身的故事也没有名字,我们不妨称之为:
图师
要把故事说清楚,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头到尾讲一遍。不是吗?想让一个人掌握故事梗概(不管这位听众是他人抑或自己),最好逐字逐句说清。然而,此举虽然巧妙,却十分不切实际。地图越精确,便越接近真实地貌。最准确细致的地图莫过于地貌本身。然而精确如是,地图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逐字逐句的故事就是一张巨细无遗的地图。
请务必牢记。
两千年前,中国有个皇帝,极度痴迷于绘制治下疆域。他在御花园中建有岛屿一座,用以安放华夏境内缩微实景。工程耗资颇巨,也捎带搭进几条人命。(要知道,湖水又深又冷。)岛上,每个土丘都是王土上一座峻岭,每条涓流都是国界内一条大河。皇帝沿岛步行一周,就要花去四分之一时辰。
清晨破晓之前,天空依然暗淡。每天,一百名男子洑过深水,蹚过浅滩,趁此时上岛。景观中如有遭天气或野鸟毁坏之处,他们必悉心维护。国内凡有水祸、地震、山崩,也靠他们移去冗物,细加调整,以求岛上王土一丝不苟。一来一去,不免有人溺于湖中。
大半年来,皇帝再无他求。可后来,龙心之中对小岛不悦渐生。就寝之前,他开始计划另一张地图:这张图大小可比天朝江山百分之一,每间小屋,每户住家,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座小丘,每头野兽……高矮大小尽取百分之一。
计划空前宏大,非倾尽税收国库之力不能成。所需人力超乎想象:图师,测绘师,勘察师,画匠;以及铸模师,陶艺师,砖瓦匠,手艺人……不胜枚举。此外,还须有六百名梦师,专司幻想树根不能探及之处、山间洞窟幽闭之处、海下沟壑深邃之处那种种玄妙,以为制图之用。凡王土之上,即使肉眼难见之物也须收入其中,此图方算善始善终。
皇帝计划已毕。
一天晚上,当朝宰相陪伴御驾,在园中散步。空中一轮满月,如金如幻。宰相直言进谏道:
“圣上,请三思,此番工程……”
一言甫出,宰相突然失去勇气,于是再无下文。一尾银鲤扰乱水面,月影纷乱,碎如片金,每一片都是一轮小小圆月。不多时,水波渐平,众月融为一道金轮。四周水色若夜,一派瑰丽深紫,与纯黑迥异。
“事不能成?”皇帝也不动怒。然而,帝王每多一分温和,便多一分危险。
“皇上有愿,岂有不成之事?”宰相说,“然而此举耗资甚巨,国库必为之倾;占地甚广,城池必为之空,田地必为之荒。事成之后国力贫乏,恐后世无以为治。臣既身为一国之相,若不直言进谏,实属玩忽职守。”
“此言抑或有理。”皇帝道,“然而,若依卿之言,朕将制图计议抛诸脑后,此事再不能成。朕之心力处世必不堪其扰,珍馐无味,佳酿如水……”
皇帝按住话头。御花园深处有夜莺清啼。再开口时,他坦言道:“然而此图仅为工程之始,行工事之时,朕仍有另一宏愿,须精心设计,方为传世之珍。”
“不知陛下所言何物?”宰相却也问得波澜不惊。
“另一份地图。”皇帝道,“凡我天下,皆依真实尺寸再现。山以山示,木以木标,大小种类一般无二。以川为川,以民为民。”
宰相身披月光,一揖到地,他随驾向宫内走去,依礼落后王上数步,一路深思。
史书有云,皇帝于睡梦之中驾崩。此言诚然非虚。不过,若说陛下纯属自然死亡却也不甚确凿。太子即位称帝。新帝对地图与制图均兴趣寥寥。
湖心小岛成为野鸟与水禽的乐园。此处全无人迹侵扰。泥山被它们衔走筑巢,岛体也遭湖水日夜冲蚀。最后,岛上种种尽忘于世,唯余一湖碧水。
地图不再,图师不再,唯山河依旧。
纪念与珍宝
这篇故事副题为“爱情故事一则”。它(或者说其中一部分)原先是一部漫画脚本,是给奥斯卡·扎瑞特(Oscar Zarate)编辑,沃伦·普里斯(Warren Pleece)作画的黑色选集《伦敦本黑暗》(It's Dark in London)写的。沃伦画得很棒,我对故事却不大满意。不知道这个自称史密斯的家伙为什么长成这样。恰逢阿尔·萨兰托尼奥(Al Sarrantonio)编辑《999》选集时找我约稿,我就想:再拜访一次史密斯和爱丽丝先生也挺好玩。顺便,他们俩也友情客串了本书另一则故事。
我想关于史密斯先生这位坏人,还有很多好料可挖,其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他与爱丽丝先生分道扬镳的故事。
芬奇小姐失踪案实录
有一次,别人给我看了张法兰克·弗拉泽塔(Frank Frazetta)的画,让我看图写故事。画上是个有老虎陪伴左右的姑娘。我实在编不出故事,就把芬奇小姐那件真事拿来充数。
怪姑娘
其实是十二个微型故事,原先是为托丽·阿莫斯(Tori Amos)的《怪姑娘》专辑配的。写作过程中辛迪·雪曼(Cindy Sherman)给了我不少灵感。托丽的歌也助益良多,她赋予每首歌不同的个性,我便为它们各写了几句。这篇东西之前没有任何选集收录,只在巡演手册中发表过。另外,随专辑附赠的小册里也摘取了篇中词句,散印于册中各处。
哈勒昆情人[6]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很欣赏莉萨·斯奈灵·克拉克这位雕塑艺术家。有本叫《奇异吸引》(Strange Arraction)的集子,是为丽萨做的摩天轮雕塑写的。很多出色的作家都在写吊篮里的游客。他们问我,给那个笑脸哈勒昆打扮的卖票人写个故事怎么样?
事就这样成了。
一般来说,故事不会自己成书。不过这一次,我记得真正出自我手的只有第一句。接下来倒更像做听写。哈勒昆兴高采烈,蹦蹦跳跳,自个儿打发他的情人节,我则奋笔疾书。
说来,哈勒昆是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角色。他是不露真容的恶作剧行家,面具遮颜,手持魔杖,穿菱形格子戏服。哈勒昆深爱柯龙比娜,戏中始终追逐她的芳踪,一路上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他的老对手包括矮胖的医生和小丑皮耶罗。
金发姑娘
《金发姑娘与三只熊》这个故事最早来自诗人罗伯特·索西(Robert Southey)。不过这么说也不准确,他那版故事里,三只熊还是三只熊,金发姑娘却是个老奶奶。当然,故事形式和经过还是一样的。后来人们觉得,小姑娘当主角比老太婆强。于是再有人讲故事时,就加了个女孩子进去。
话说回来,童话是代代相传的。你可以去找童话,童话也会上门寻你。童话是我们这一代与先人共享的财富。(我给我的孩子讲故事,以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给我讲故事。这种感觉很特别,很奇异,仿佛我已经融入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成为它的一部分。)我给麦蒂(我的女儿)写这篇东西时她才两岁,可现在已经十一岁了。我们还会共享故事,一起看电视,一起看电影,看一样的书,聊一样的书……可是,我再也不会念故事给她听了。再说,与其念别人的故事,自己为她编故事又要好上许多倍。
我相信分享故事是我们的责任。无论过去将来,这恐怕是我仅有的人生信条。
苏珊的问题
旅馆给我叫了医生。医生说,是流感这坏蛋,让我头疼欲裂,吐个不停,又难受又郁闷。接着,他列出一堆止疼药和肌肉松弛剂。我挑了种止疼药,就跌跌撞撞地缩回旅馆房间,倒头昏了过去。动弹不得,无法思考,连头也抬不起来。第三天,私人医生从家里打电话来,好生叮嘱了洛琳(我的助手)一番,又对我说:“我不喜欢不见病人,光靠电话做诊断,可你得的是脑膜炎。”他是对的。我得的正是脑膜炎。
又过了好几个月,我终于头脑清醒,可以重新写作。落笔之后第一篇作品就是《苏珊的问题》。整个过程仿佛在蹒跚学步。这个故事是为阿尔·萨兰托尼奥(Al Sarrantonio)的幻想小说集《飞》(Flights)写的。
小时候我把纳尼亚传奇系列小说看了几百遍,长大后又两度念给孩子听。故事里太多东西我都爱得不得了。可是,每次看我都会想,书里对苏珊的处理实在很成问题,让人生气。当时我想:一定要写一个同样问题多多、叫人生气的故事(当然,毛病要出在不一样的地方),还可以顺笔写一写儿童文学那惊人的力量。
指南
上一本短篇集《烟与镜》中已包括几首诗。我原计划这本《易碎品》里只收小说,可是,最后还是忍不住加进几首诗来。主要原因就是:我实在太喜欢《指南》了。如果你就是不喜欢诗,也可以略感欣慰。你看,这些诗和本篇简介一样,都是免费赠品。少了它们本书也不会减价,加了它们也没有人多发我稿费。有时候,顺手捡起几行字读一小会儿也不错。同样,看这篇简介,了解一点故事背后的故事,这也很有趣,看不看故事本身随你。(另,虽然我高高兴兴地自我摧残了好几星期,才定下本书里文章的先后顺序,但先看哪篇完全随你高兴。)
至于本诗,文如其名,哪天你发现自己掉进童话世界,它就是你的指南。
感受
有人让我给一个以石像鬼为主题的选集写个故事。截稿日就要到了,我大脑还一片空白。
我想到,石像鬼是教堂屋顶上的守护者。那么,或许它也可以待在别处,保护其他东西,比方说,我们的心。
八年后,我第一次重读此文,文中的性爱描写让我有些吃惊。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本来就对这一篇不太满意吧。
这辈子
这篇诡异的小独白是为摄影家阿恩·斯文森(Arne Svenson)的摄影图书写的,配在一张玩具猴照片边。整个集子里共有两百张玩具猴图片,该书也毫无悬念地叫作《玩具猴》(Sock Monkeys)。分给我那张图里的猴子好像很命苦,不过日子过得一直很有趣。
有位老友刚开始给《世界新闻周报》(Weekly World News)写稿。我有时帮她编些故事,倒也乐在其中。不知道大千世界上,有没有人把日子过得跟《世界新闻周报》一样。《玩具猴》一书里,这篇是按短文格式印的,不过我觉得分成一行一行效果更妙。我相信,只要点上足够的酒,再加一位好听众,这个故事可以永远永远讲下去。
(说来,偶尔有人在我的网站上留言,问能不能借这篇做他们的试演表演材料,也有问其他作品的。尽管用,我不介意。)
吸血鬼塔罗十五张
要凑满全套大阿卡那牌,还得再写七个故事。我和艺术家里克·贝里(Rick Berry)达成协议,将来我一定完稿,他则负责为我配图。
饲者与食者
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二十来岁时做的噩梦。
我喜欢梦。不过,我很清楚,梦有自己的逻辑,和故事不同,直接把梦写成小说往往极难成功。明明梦中感觉良好,一旦睁眼却难免真金变废铁,珠玉变顽石。
梦会给你留下不少灵感:梦中气氛、片段、人物,甚至主题,均可借用。不过,只有那一次,我从梦中成功收获一个完整的故事。
第一稿本来是篇漫画,由多才多艺的马克·白金汉(Mark Buckingham)绘制。后来,我尝试着把它改成三级恐怖片脚本,却从没找到开镜的机会。(我连名字都想好了,叫《吞噬:来自银幕》。)几年前,编辑斯蒂夫·琼斯(Steve Jones)跟我说,有些老故事不该就此被历史遗忘,可以考虑挖出来,贡献给他的《拒绝夜色》(Keep Out the Night)选集。我想起这篇东西,于是卷起袖子,说改就改。
鬼伞菇的确非常美味。不过摘下来以后,这种蘑菇会很快变成恶心的一摊黑水,指望饭店是没戏了。
造病者喉炎
有本叫《赛克里·T.拉姆谢德奇病异症随身读本》(The Thackery T.Lambshead Pocket Guide to Eccentric and Discredited Diseases)的集子,由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和马克·罗伯茨(Mark Roberts)编辑,专门记录假想病症。我觉得,如果有这么一种怪病,患者症状就是喜欢捏造怪病,一定挺有趣的。以下两件东西对本文写作助益颇大:一个我很久不碰的计算机程序,叫作“胡话生成器”,一本落满灰尘的精装家庭医生手册。
尾声
这篇是我想象中的圣经终章。
一说到给动物命名,就想起喜马拉雅山“雪人(yeti)”来。如果按字面翻译,“雪人”应该叫“那边的东西”。这实在叫我乐不可支。请想象以下对话:
——快来,勇敢的喜马拉雅向导啊,那边的东西是什么?
——那边的东西(yeti)。
——哦,我知道了。
歌利亚
数年前,我的助理说:他们想拜托你写个故事,一个电影网站要用。那电影还没公映,叫《黑客帝国》,他们会把剧本发给你。于是,我兴趣盎然地读完剧本,写了这个故事。公映前一周左右,它出现在电影主题网站上,今天你仍可以在那儿看到。
某乘客由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乘灰狗巴士至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时遗落车上一鞋盒中觅得之日记·摘录
本篇乃是几年前为吾友托丽·阿莫斯(Tori Amos)的巡演手册《绯之行》(Scarlet's Walk)所作。后来有本最佳短篇年选收了它,让我高兴极了。这个故事从《绯之行》中得到一些零星灵感,我想写的是一则关于身份替代和美国风土的旅途故事。它有点像《美国众神》的姊妹短篇,文中,一切(包括问题的答案)都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给男生的派对搭讪指南
对我来说,故事的诞生过程往往十分有趣,不亚于收获最后成果。比方说,这则故事脱胎于两篇失败的底稿。当年,澳大利亚批评家乔纳森·斯崔汉(Jonathan Strahans)编辑《星隙》(The Starry Rift)时找我约稿。(这篇搭讪指南在本书中算是初次付印,《星隙》中没有收录。希望以后我能给乔纳森另写个故事。)构思之后,落笔时并不顺利,我只折腾出一些毫无意义的粗糙片段,最后不得不满头晦气地给乔纳森写邮件,告诉他故事没戏了,至少我这儿已经交稿无望。乔纳森回信说,他刚刚拿到篇好稿子,是一位我很佩服的作家写的。她只用二十四小时就顺利完稿。
一听此言,我恼羞成怒,打开空本子,拿出笔,钻到花园露台上,憋了一下午,写出这个故事。几周后,我第一次拿它当众朗读,是在传说中的CBGB俱乐部[7]。活动是公益性的。鉴于故事背景是朋克风潮,叛逆的1977年之类,CBGB确为不二之选,实在叫我高兴极了。
飞碟造访之日
我灌制有声书《星尘》那周,在纽约旅馆房间里等车来接时写了这首小诗,起因是编辑兼诗人瑞因·格瑞夫(Rain Graves)让我给她的网站www.spiderwords.com写几首诗。后来当众朗诵效果不错,我也很开心。
太阳鸟
我大女儿霍莉过十八岁生日时,明明白白地找我索要生日礼物。她说,我要一件只有你能给我的东西,爸爸。给我写个短篇吧。鉴于她对自己父亲的禀性了如指掌,说完马上又加了一句:不过你是个拖稿王,我也不想催你,只要我十九岁生日前看到,就算完成任务。
曾经有位作者住在塔尔萨,2002年去世。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阵子,这位拉菲尔·A.拉弗蒂先生(R.A.Lafferty)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的故事怪诞离奇,无法分类,个性十足,往往没看完一句就能猜出作者。年轻时我给他写过信,还收到过回信。
当初写《太阳鸟》,我模仿的就是拉弗蒂,写作过程中收获颇多,许多技巧真正操作起来要比想象的难多了。霍莉直到十九点五岁生日才拿到礼物。那时我写了一半《蜘蛛男孩》,只觉若不找点短平快的东西写写,脑子都要坏了。后来这篇东西发表在一本名字奇长无比的集子里。(当然有霍莉批准在先。)该书是文学公益活动计划之一,书名常简称为《吵死人的强盗、不友好的怪物,以及其他略逊一筹的骇人物》(Noisy Outlaws,Unfriendly Blobs,and Some Other Things That Aren't As Scary)。
虽然你已经买过本书,倒也不妨再收一本《吵……》。里面克莱门特·弗洛伊德(Clement Freuds)那篇《格林伯》(Grimble)还是不错的。
创造阿拉丁
有一件事总叫我大惑不解(说好听点叫大惑不解,其实说白了就是——叫我火冒三丈)。有些大部头学术著作,研究方向是民间传说和童话,我经常拿来看。它们宣称,民间故事本无作者,追溯其源头、探寻其作者实为大谬。此类著作论文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所有老故事都是半路捡来的,要么就是在原型基础上修修改改。我想,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故事皆有起源,最初总诞生于人类脑海之中。原因很简单——故事是人编的,与客观景物、自然现象之类不同。
我看过这么一本专家论著,书里阐释,凡提到有角色睡着的童话故事,都脱胎于原住民的梦境。祖先们从梦中醒来,对别人讲述梦境,因为智力太过蒙昧,不能区别梦与现实,便将睡着前后的经历合为同一故事。这便是童话的起源。这种专家理论实在漏洞百出,立论便大成问题。因为,代代相传,流传到今天的故事都有起承转合良好的特点,与梦境逻辑截然不同。
故事都是人编的。有人爱听,就流传下来。这就是它的魔力。
山鲁佐德本是虚构人物。需要每夜以故事降服的暴君,山鲁佐德的妹妹……这都是假的。《一千零一夜》本身就是故事,包含了各地收集来的元素。阿拉丁这个故事出现得比较晚,几百年前才由法国人加进《一千零一夜》中去。换句话说,“创造阿拉丁”这段历史一定和我写的不一样。我的故事不存在于历史,也不存在于未来。
山谷君王
这篇故事脱胎于我对苏格兰偏僻野地的挚爱。那里,大地的脊梁一览无余,天空苍白,一切美得令人窒息。那是世界上最荒凉、最辽远的地方。《美国众神》完结两年后,我也很高兴与影子重逢。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让我给第二本《传奇》(Legends)选集写个中篇。他说,用《乌有乡》或者《美国众神》背景写都无所谓。写《乌有乡》中篇时我遇上些技术问题,暂时停笔。(那篇东西叫《侯爵大衣寻回记》,我以后会写完的。)后来,去诺丁山导演一部叫《约翰·博尔顿短片》的微型电影时,《山谷君王》诞生了。我在湖边小屋里狂写了整整一冬,终于大功告成。顺便一提,眼下我正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写这篇导言。吾友伊丝琳·伊文森(Iselin Evensen)是挪威人。我最早就是从她那里听说了山鬼的故事。她还教过我挪威语。和《烟与镜》中的“湾狼”(Bay Wolf)一样,本文也深受《贝奥武甫》影响。说来,写《山谷君王》时,我还以为以前受罗格·阿维里(Roger Avary)之邀,和他合写的《贝奥武甫》电影脚本铁定黄了。事实证明我错了。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ckis)版电影中,安吉丽娜·茱莉的形象和本文中的格伦德尔之母相去甚远,实在很有意思。
(张秋早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