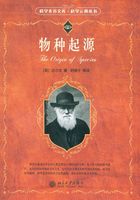
生存斗争中动植物间的复杂关系
许多报道的事例都可证明,同一地区内互相斗争的生物间,存在着十分复杂和出乎预料的抑制作用和相互关系。仅举一个简单但我觉得极为有趣的例子: 在斯塔福德(Staffordshire)郡我亲戚的一片土地上,我曾作过仔细的调查,那里有一大片从未开垦过的荒地,还有数百英亩性质完全相同的土地,在25年以前曾围起来种植苏格兰冷杉。在种植过的这片土地上,原来的土著植物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是在两块土质不同的土地上也看不到这么大的差别。和荒地比起来,这里植物的比例完全改变了,而且这里还繁茂地生长着12种荒地上没有的植物(不计草类)。植树区内昆虫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有6种在人造林带中常见的食虫鸟类在荒地上没有,而经常光顾荒地的两三种食虫鸟,在人造林中也没有见到。当初把种植区围起来是为了防止牛进去,此外并无其他任何措施,可见引进一种树竟产生了这么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萨利(Surrey)的法汉姆(Farnham),我也曾清清楚楚地看到对荒地进行人工圈围作用的重要影响。在那片宽广的荒地上,原先只有远处小山顶上有几片老苏格兰冷杉林。在最近十年内,有人把这里大块大块的荒地围起来,结果使在围地中的冷杉自行繁殖,无数的小杉树长出来。在确信这些小树并非人工种植时,我对这些小杉树的数量之多感到惊奇。于是我又观察了几处地方,发现在上百英亩未圈围的荒地上,除了以前种的老冷杉树外简直找不到一株新生的苏格兰冷杉树。但是当我仔细观察荒地上的树干时,发现无数的杉树苗和幼树都被牛吃掉而长不起来。在距一片老冷杉树数百码远的地方,我从一平方码的地面上数出了32株小冷杉树,其中一株有26圈年轮了,但是多年来它始终不能把树干长得比荒地上的其他树木高。怪不得荒地一旦围起来,立刻就会长满生机勃勃的小冷杉呢。可是谁能想到,在这荒芜辽阔的地面上,牛会如此仔细而有效地搜寻冷杉树苗当作自己的食物呢。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牛完全控制着苏格兰冷杉的生存。然而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昆虫又决定着牛的生存,在这一方面,巴拉圭(Paraquay)的例子是最稀奇的了。该地从未有牛、马、狗变成野生的情况,虽然该地区的北面和南面,都有这些动物在野生状态下成群地游荡着。阿萨拉(Azara)和伦格(Rengger)曾指出,在巴拉圭有一种蝇,数量极多,而且专把卵产在刚初生动物的肚脐中。这种蝇虽多,但它们的繁殖似乎受到某种限制,可能是别的寄生昆虫吧。因此,在巴拉圭如果某种食虫鸟减少了,这些寄生昆虫就会增加,在脐中产卵的蝇就会减少,那么牛和马就会变成野生的,而这肯定又会极大地改变植物界(在南美的部分地区我确曾见过此类现象)。接下去植物的变化又会影响昆虫;而后,正如我们在斯塔福德郡看到的那样,受影响的将是食虫鸟类,以此类推,复杂关系影响的范围就越来越广了。其实自然状态下动植物间的关系远比这复杂。一场又一场的生存之战此起彼伏,胜负交替,一点细微的差异就足以使一种生物战胜另一种生物。但是最终各方面的势力会如此协调地达到平衡,以至于自然界在很长时间内会保持一致的面貌。可是对于这一切,人们往往知之甚少,而又喜好作过度的推测。所以在听到某一种生物绝灭时,不免感到惊奇,在不知绝灭的原因时,便用灾变来解释世界上生命的毁灭,或者编造出一些法则来测定生物寿命的长短。
我想再举一例,以证明在自然分类上相距甚远的动植物,是如何由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联系在一起的。在我的花园里,昆虫从不造访一种外来的墨西哥半边莲(Lobelia fulgens)。结果,因这植物的构造奇异,它在我们的花园里就不能结籽,以后我还会有机会再来说明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兰科植物都需要昆虫传授花粉才能受精。试验中,我发现三色堇(heartsease, viola tricolor)的受精,必须靠野蜂(humble-bees)完成,因为别的蜂不去采这种花粉。我还发现某些三叶草(clovor)的受精也离不开蜂来传播花粉。例如,白三叶草(Trifolium repens)的20串花序可结2290颗种子,但另外20串花序被遮盖住,不让蜂类接触,于是一颗种子也不结。又如,100串红三叶草(Trifolium pratense)可结种子2700颗,而遮盖起来同样多的花序也是一籽不结。只有野蜂会来光顾红三叶草,因为别的蜂压不倒它的花瓣而采不到它的花粉。有人以为蛾类也可能使三叶草受精,但我怀疑此事,因为蛾的重量,不能把三叶草花瓣压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很有把握地推论,如果整个属的野蜂在英国绝迹或变得非常稀少,三色堇和红三叶草也会相应变少甚至绝迹。在任何地方,野蜂的数量与田鼠的多寡关系密切,因为田鼠会毁坏蜂房和蜂窝。纽曼(Newman)上校对野蜂的习性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认为英国有2/3以上的野蜂窝是被田鼠毁坏的。谁都知道田鼠的数目取决于猫的数目,因此纽曼上校说:“在村庄和城镇附近发现的野蜂窝比别的地方多,我认为那是因为大量的猫消灭了田鼠的缘故。”因此完全可以相信,如果一个地区有大量的猫,通过猫对田鼠,接着又是对蜂的干预作用,就可以知道这一地区内某些花的数量是多少。
每一物种的兴衰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都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作用。一般说来,其中有一种或数种因素的制约作用最大,但一个物种的平均数量甚至能否生存,则是由所有因素综合决定的。有时候,同一物种在不同地区,受到的制约作用也极不相同。当我们看到河岸上繁茂的树木及灌木丛时,常会以为它们的种类和数量比例纯属偶然。其实,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谁都听说过,在美洲一片森林被砍伐以后,那里会长出不同的植物群落。但是,看看美国南部的古代印第安废墟吧!当初那里的树木一定会被完全清除过,可是现在,废墟上生长着的美丽植物与周围原始森林中的植物,在物种的多样性和数量比例方面完全一致。在过去悠悠岁月中,在那些年年播撒成千种子的树木之间,昆虫之间有激烈的生存斗争;在昆虫、蜗牛、小动物与鸷鸟猛兽之间也有激烈的生存斗争!一切生物都力求繁殖,而它们又彼此相食,有的吃树,吃它们的种子和幼苗,有的吃那些刚长出地面会影响树木生长的其他植物。如果我们将一把羽毛扔向空中,羽毛会依一定法则散落到地上。要弄清楚每支羽毛应落在何方,这的确是个难题。但是这个难题与数百年来动植物间是如何作用,以至最终决定了古印第安废墟上今日植物的种类和数量比例的问题相比较,那可就显得简单多了。
在亲缘关系上相距很远的生物之间一般会出现某种依存关系,如寄生生物与寄主之间的关系;但严格地说,远缘生物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生存斗争,如蝗虫和食草动物之间的关系。不过,最激烈的生存斗争几乎总是发生于同种的个体之间,因为它们生存于同一地区,需要同样的食物,遭受同样的威胁。同一物种内各变种间的斗争几乎也同样激烈,而且有时短期内即见分晓。例如,把小麦的几个变种混合后播种在一块土地上,然后把它们的种子再混合播种在一起,结果那些最适合该地区土质和气候的变种或繁殖力最强的变种就会结籽最多,数年后就会战胜并取代其他变种。即使在极为相似的变种间情况也是如此。如,混合种植的不同颜色的芳香豌豆(sweet peas)必须分别收获,再按一定比例混合后进行播种,否则较弱的变种会逐渐减少以至消失。绵羊变种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据说某一种山地绵羊会使另一种山地绵羊饿死,所以它们不能放养在一起。在合养不同变种的医用蚂蟥(Medicinal leech)时也有过同样的情况。如果让家养的动植物在自然状态下去自由竞争,每年也不按一定比例把种子或幼体保存下来,那么六年后这个混合群体(阻止杂交)中的各种动植物,能否完全保持原来的体力、体质及习性和原来的数量比例呢?恐怕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