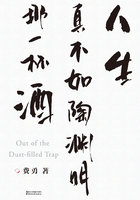
第6章 我和这个世界之间最合适的距离是什么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其五)
我住的房子就盖在纷乱的人群里,
人群里的是是非非、热热闹闹却都在我之外。
你问我怎么能让世界的喧闹在我之外,
我说如果你心远了世界就在你之外了。
此刻在东边的篱笆下采摘菊花,
不经意间抬头,看见了南山别有一种宁静风姿。
山间的云雾从早到晚都晃晃悠悠,
黄昏了,那些去远方觅食的鸟儿
结伴飞回山里自己的窝。
人生的什么真理啊什么乐趣啊,都在这幅画面里了,
我想说出来,却又忘掉了用什么语言才能说出来。
01
这首诗的前面几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写了一种人生的大境界,住在世俗社会里,却没有车马的喧闹。如果活在今天,陶渊明会说,住在高速公路的旁边,却没有汽车声;住在铁路边,却没有火车声;住在街市里,却没有嘈杂声;拿着手机,却没有铃声。
总之,住在热闹的人群里,却没有人群的热闹;住在混乱的环境里,却没有混乱。并不是没有车马声,并不是没有混乱,而是我的心不受这些声音的干扰,所以,即使很喧哗的地方,也好像是很安静的地方。如果我的心是清澈的,那么,世界再混乱,我也不会乱。
在这里,陶渊明思考的是,人如何不受环境的干扰而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换一种说法,就是如何“以心转境”?所谓“车马喧”,是象征的说法,不仅仅指车马的喧闹,而是指带有干扰性的环境因素。
人活在世界上,总是活在一定的环境里。亚里士多德说:“从本质上来讲,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任何一个不能过公共生活的人或者自给自足到无须过公共生活的人都不是社会的成员,这意味着他要么是一头野兽,要么是一个神。”
而我们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很少像鱼和水那样有鱼水情。大多数时候,我们和环境的关系更像冤家对头,吵吵闹闹,不断妥协,不断冲突。我们成长的过程,好像就是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在适应环境的过程里,有些人找到了自己,有些人却永远地迷失了自己。
所以,个人和环境如何相处,是一个人类的永恒话题。陶渊明这首诗,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触及了这个永恒的话题。
02
那么,环境如何干扰个人呢?或者说,环境有哪些喧哗对个人造成干扰呢?
第一种是最常见的,就是引起我们不适的干扰,比如噪音,比如炎热,比如恶劣的人际关系,会让我们烦躁不安。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类干扰,就会在烦躁不安里迷失自己。
第二种是相反的干扰,是更为危险的干扰,就是引起我们贪欲的干扰,比如声色犬马,会让我们快乐兴奋。我们并不会觉得是干扰,反而觉得是一种享受,但这种享受把我们降低到动物性的层面,让我们慢慢往下沉沦。如果我们不能对这种享受有所警觉,有所升华,就会是一种对生命成长严重的干扰。
第三种最不引人注意,却是最危险的干扰,就是社会成规。有时表现为流行的时尚,有时表现为主流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个人很难抵御这种干扰,大多数时候,不论我们内心多么不喜欢这种主流的东西,还是会不知不觉让自己不断适应,最后成为社会接纳的人。大多数人都在适应社会成规里草草走完一生。只有少数人能够跳出社会成规,活出自己。
03
如何应对环境的干扰呢?陶渊明的回答是“心远地自偏”。如果心远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干扰我们;如果心远的话,住在哪里,哪里就是安静的所在。
一下子把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不要去管环境怎么样,不要去管活在唐朝还是民国,不要去管活在美国还是中国,不要去管冷还是热,不要去管社会风气如何败坏,而是要管好自己的心。
这句话非常励志,强调了个人的作用。在环境和人的关系里,我们往往屈服于环境的压力,往往被环境改变。但陶渊明说:“心远地自偏。”这句话涵盖了东方思想的基本信念:个人凭借心灵的力量可以改变环境。也就是古语里常说的“以心转境”。
怎么样以心转境?陶渊明的答案就一个字:远。好像很容易理解,又好像很难理解。一个普遍的误会是,人们常常把“以心转境”理解成心念可以改变具体的场景。比如,我们住在高速公路旁边,只要我们心静,什么噪音都无所谓。但事实上,当噪音超过一定的分贝,不论你心多么静,都不会让噪音消失,都不会阻碍噪音震聋你的耳朵。这个时候,你要么通过装隔音设备解决噪音的问题,要么离开,去另一个安静的地方。
如果机械地理解“心远地自偏”,那么,陶渊明自己也没有必要离开“官场”。因为只要心怀高洁,哪里都一样。但事实上,如果官场违背我们自己的心性,那么,我们留在那里,就是让自己陷在了泥潭里,最后成为烂泥。莲花确实生长在污秽的泥潭,但它一心努力向着洁净的水面生长。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安迪不论怀着多么自由的信念,也不可能把监狱本身变成自由的所在,但是,他坚定的信念最终让他离开了监狱,自己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环境。
陶渊明再高洁,也不能改变官场的实质。莲花再高洁,也不能改变污泥的性质。能够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心,让它不受到污染,只是我们自己可以逆行而上,找到另外的生存方式。
所以,陶渊明的“远”,有离开的意思,也有保持距离的意思。离开什么呢?离开一切和自己的本性相违背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多么热闹多么荣耀,如果它们违背我们的本性,就一定要离开它们。
所以,心远,就是心不受任何环境因素的影响,知道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可改变的,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谓个人的心灵可以改变环境,并不是指个人透过心念就可以改变具体的环境,而是指自己的心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自己找到或创造适合自己的环境。
04
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历程里,“心远”指的是不受环境的干扰,通过改变、离开等方式,自己创造自己的现实。在陶渊明的这首诗歌里,“心远”又不完全是指整个的生命历程,而是一个当下的片刻。
有一个背景也许有助于理解这首诗歌。什么背景呢?就是陶渊明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彻底辞官,彻底过着农夫的生活。在那个年代,不论那种生活多么贫穷、多么困顿,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只能安于这种生活。至少,这种生活不会像官场的生活那样违背自己的本性。
农夫的生活,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陶渊明在无可选择的困顿里,安于当下,活出了另一种韵味。这是“心远”的另一个意义,即使在仿佛毫无选择的困境里,我们的心如果对于这种困境保持距离,那么,心还是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所在。
陶渊明这首诗的下半段,就写了困顿生活里的一个片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刻我在采摘菊花,南山、飞鸟、云雾,都是偶然相遇,也是有缘相遇,遇到了就遇到了,我忘掉了用什么语言去描述此情此景。我只觉得此刻多么安静多么美好。还需要说什么呢?
此刻多么安静多么美好,心远地自偏。引导我们在每个当下向着自然敞开,向着本源敞开,放下一切的分别心,享受此时此刻。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此刻,我还是享受世间的光与影,还是怀着清洁的念头让生命盛开。
05
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这首诗是陶渊明最有名的一首诗,也常常被认为是隐士飘逸生活的写照。隐士的生活多么悠闲啊,每天就是采采菊花,看看山。但事实上,这首诗不过是很平实的生活再现,一点也不轻松。或者说,轻松潇洒之下,暗涌着人生的无奈和痛苦。又或者说,这首诗不过写出了:人生再无奈再痛苦,还是要活得轻松和潇洒。
陶渊明不愿意当官,回到田园,严格地说,不是隐居,而是换一种活法。他的辞官,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因为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所以,他辞了官,不是躲到深山里去,与鸟兽为伍,而是回到家里,和妻儿一起,过着农夫的生活。所以,他的房子还是在人世间,他还是活在人世间。这首诗不是一个隐士的飘逸情怀,而是生活在生活里的一个当下感悟。
这个感悟很容易被理解成心能转境。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结合陶渊明的生平,再来细读这首诗,或者把这首诗和《归田园居》结合起来读,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体会。什么体会呢?就是在东方的思想体系里,所谓以心转境,其实是心境一体。并没有心和境的分别,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就如佛学里所言:“心不自心,因境故心;境不自境,因心故境。”又如《维摩诘经》也说:“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法藏法师则说:“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这几句好像很玄妙的话,如果我们真正领悟了,就会成为一种大智慧,让我们彻底远离分裂、纠结的生活状态,而活在自在无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