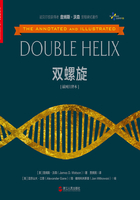
![]()
05
转投剑桥
后来,我放弃了想要与威尔金斯合作研究的想法,但他的DNA照片却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把有可能解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我绝不会将它从我的头脑中剔除出去。我还不能解释它,但我并不因此感到烦恼。设想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科学家,要比设想自己成为一个从来不敢冒险提出独创性观点的、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我也曾因鲍林部分地解决了蛋白质结构的传闻而深受鼓舞。那时,我正在日内瓦与瑞士噬菌体学家琼・韦格尔(Jean Weigle)讨论问题。他刚刚结束了长达一个冬季的访问研究,从加州理工学院回到了瑞士。在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之前,韦格尔参加了鲍林宣布那个消息的报告会。

琼·韦格尔,摄于1951年
鲍林在报告会中采用了他惯常的舞台表演式的讲演方法,他在讲演时就像一个终生从事演艺事业的表演艺术家。在那次讲演过程中,他的模型一直被一块帷幕掩盖着,直到讲演即将结束时,他才骄傲地向观众展示了他的最新成果。然后,鲍林目光炯炯地向大家解释了他的模型——α-螺旋模型——的各种特征,这些特征使他的模型美得无与伦比。

鲍林的α-螺旋模型

莱纳斯·鲍林与他的原子模型
那是一场表演,就像他以往所有的精彩报告一样,鲍林的讲演吸引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前来参加。像鲍林那样能紧紧抓住听众的人,全世界都不可能再找出第二个了。他把不可思议的头脑和极具感染力的露齿微笑完美地结合起来,魅力之大,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鲍林的许多教授同事也怀着复杂的心情观看了他的讲演。鲍林在演示台上不断地跳上跳下,同时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就像一个随时都可能从靴子里掏出一只兔子来的魔术师。这场景使得他的同事们相形见绌。如果鲍林表现得稍微谦虚一点,那么他的观点也许会更容易被人接受。由于他表现出了极其坚定的自信心,所以即使他是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不会了解。而他的许多同事则在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待着他在重要问题上栽个大跟头、摔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天。

鲍林、罗伯特·科里(Robert.Corey)和布兰森在1951年4月15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α-螺旋模型
那个时候,韦格尔并不能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模型是否正确。韦格尔不是X射线结晶学家,无法从专业角度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比他更年轻、在结构化学方面训练有素的朋友却认为,α-螺旋模型看起来相当不错。因此,韦格尔的朋友们给出的结论是,鲍林是正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鲍林又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生物学中极其重要的大分子结构而言,他可能是揭示出正确模型的第一人。因此,我们有理由想象,鲍林在此过程中也许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新方法,可以推广适用于核酸结构研究。然而,韦格尔却根本不记得鲍林的方法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所能告诉我的,无非是有一篇描述α-螺旋结构的论文不久之后就会发表。
当我回到哥本哈根时,载有鲍林论文的那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已经从美国寄到。我很快地浏览一遍,然后又立即重读了一遍。对于论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我都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只是对他的论点有一个大致印象。当然,我无法判断鲍林在这篇论文中说的东西是否成立,敢肯定的只有一点,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又一期刊载了鲍林的7篇论文的杂志寄到了!这些论文所用的语言华丽得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同样充斥着修辞技巧。其中一篇论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法启发了我。我开始构思,如果我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在撰写关于DNA的论文时应该怎样开头。我想,如果我的论文的起首句是“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那么就可以将我的思路与鲍林的思路清晰地区别开来了。

1951年5月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目录。注意,前7篇论文的作者都是鲍林和科里
我开始为下一个问题忧虑起来:到什么地方去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的技术呢?到加州理工学院去恐怕不合适,因为鲍林太伟大了,他不可能浪费自己的时间去教一个缺乏数学训练的生物学家。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再次用热脸去贴威尔金斯的冷屁股。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去英国剑桥大学了,我了解到剑桥大学有一个名叫佩鲁茨的科学家,他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血红蛋白的结构非常感兴趣。于是,我给卢里亚写信,告诉他我最近涌现出了研究DNA的激情,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安排到剑桥大学佩鲁茨的实验室去学习。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这件事竟然完全不是问题。收到我的信之后不久,卢里亚就参加了一个在安阿伯(AnnArbor)召开的小型会议,在那里他遇到了佩鲁茨的合作者——约翰・肯德鲁(John Kendrew)。当时肯德鲁正在美国进行长期旅行。更加幸运的是,卢里亚对肯德鲁的印象非常好。像卡尔卡一样,肯德鲁很有教养,而且也支持工党。更巧合的是,当时剑桥大学实验室刚好缺人,肯德鲁正在物色能够与他一起研究肌红蛋白的合适人选。卢里亚便向他举荐,说我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并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

约翰·肯德鲁
那时已经到了8月初,距离我原来的奖学金到期的日子刚好只剩一个月。这意味着我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立即动手给华盛顿有关方面写信,告诉他们我改变学习计划的事。但我仍然决定再拖一下,等到剑桥大学实验室正式接受我前往时再写这封信。事与愿违的可能性永远无法排除,因此出于慎重考虑,我认为在与佩鲁茨讨论过之后再来写这封很难下笔的信为好。与佩鲁茨讨论过之后,我就能更加详尽地说明我渴望在英国实现的目标了。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哥本哈根, 相反,我暂时又回到了实验室,做了一些以“第二等”的标准来看还算有意思的实验。决定先留在哥本哈根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很多研究噬菌体的学者都会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当然,其中也包括德尔布吕克。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进行的研究,他应该会带来更多的消息。
相反,我暂时又回到了实验室,做了一些以“第二等”的标准来看还算有意思的实验。决定先留在哥本哈根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很多研究噬菌体的学者都会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当然,其中也包括德尔布吕克。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进行的研究,他应该会带来更多的消息。
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带给我更多的新消息。他认为,即使α-螺旋模型是正确的,在生物学上也算不上什么深刻洞见。看起来,对于这个模型,他似乎根本不想多谈。甚至当我对他说,有人确实拍出了一张非常出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时,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期间,尼尔斯·杰尼在家里举行的一个派对,摄于1952年9月
不过,德尔布吕克直率的性格并没有令我觉得特别沮丧,因为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空前成功。参加会议的几百名代表抵达后,他们享用着无限量供应的免费香槟(部分由美国出资赞助),大会组织者希望这样可以消除或减轻各国代表之间的隔阂。
整整一个星期,主办方每晚都安排了招待会、宴会以及海滨酒巴狂欢的午夜之旅等活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此之前我一直将这种生活与腐朽的欧洲贵族阶层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一个重要的真理逐渐在我的头脑中扎下了根:科学家也完全可以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不仅在知识探索方面,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如此。就这样,带着美好的心情,我精神饱满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哥本哈根蒂沃利公园中的一个酒吧,摄于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