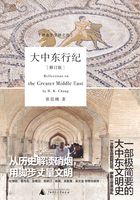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非洲之角的雄狮
“Coffee”与“Kaffa”
1963年7月,我从台湾到埃塞俄比亚的贡德尔;月底,顺利地拿到了美国签证。我当然万分欣喜,给我签证的领事却说这是他的幸事。这不但是他第一次给要去斯坦福大学的留学生做英语口试,也是他第一次发签证给中国学生。此后一个月,这名中国学生几乎成了“社交蝴蝶”,晚上参加不少家庭“派对”,白天一会儿和埃塞俄比亚小伙子们打篮球,一会儿跟伊朗姑娘学骑马,一会儿又跟以色列医生开车走访小乡村。
当然我也学到不少。埃塞俄比亚的主食称为“injera”,是大麦发酵后烤成的略带酸味的松软大薄饼;进餐时肉类和蔬菜放在饼上,用手撕下一小块饼,包着菜往嘴里送。餐后必喝咖啡,因为埃塞俄比亚是咖啡的原产地。我学到,咖啡先是从埃塞俄比亚传到也门,然后传到伊斯兰朝圣之地麦加,再由麦加传播到整个中东地区。16—17世纪时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咖啡传到欧洲各地。今天,除了埃塞俄比亚,全世界都把这种饮料称为咖啡,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卡发”(Kaffa)地区至今仍然漫山遍野都是咖啡树。
我也知道了尼罗河八成以上的水量来自青尼罗河,而它的源头就在贡德尔以南一百多公里的塔纳湖。埃塞俄比亚和埃及早在五千年前就有了贸易,但当时的路线可能是沿着红海而不是沿尼罗河来往。埃及人将红海西岸的地区,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称为“邦特地区”(Land of Punt)。
8月底,我告别父母,到厄立特里亚的首府阿斯马拉(Asmara)三日,主要是为了治一颗发炎的门牙,也顺便游览了这个曾被意大利刻意建设的新城市。这三天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倒不是比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更为现代化的阿斯马拉,而是红海之滨的古旧小城市——当时埃塞俄比亚的唯一海港马萨瓦(Massawa)。
我从阿斯马拉乘飞机经喀土穆(Khartoum,苏丹首都)、开罗、雅典、罗马、苏黎世和巴黎等地略作游览,再搭机去纽约。
安内与攘外
经联合国通过,埃塞俄比亚与前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Eritrea)于1951年组成联邦;1962年埃塞俄比亚把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曾经被意大利统治将近半个世纪的厄立特里亚强行改为一个行省,引起许多当地人不满,于是出现了厄立特里亚独立运动。埃塞俄比亚政府以高压手段对付。
当时埃塞俄比亚的邻国有苏丹、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兰(即吉布提)和肯尼亚。它和前二者有边界纠纷及跨界民族的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是英国统治苏丹时和意大利统治索马里时留下来的;一部分也是因为位处“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包括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包括法属索马里兰)自古就是亚、非之间频繁交往的地区。埃塞俄比亚要想在“非洲之角”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就必须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这两个面海地区维持控制力。

贡德尔城外一景(1963年)
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苏丹人和索马里人分别住在西部和东部,他们彼此的形貌和语言不同,却都是穆斯林。因此他们一个朝西、一个朝东的离心力给占统治地位、信奉基督教的阿姆哈拉族人相当大的威胁。此外,埃塞俄比亚境内还有几十个信仰传统自然宗教而语言各不相同的民族。这是任何埃塞俄比亚政府必须面对的内政难题。
在阿姆哈拉民族内部,贵族骄纵专横,官僚贪污弄权,百姓蒙昧无知。我当时的印象是,一般阿姆哈拉族的年轻人既不满他们的统治者,也无法与反对阿姆哈拉族统治的其他民族团结。贡德尔医学院里占主流的基督教学生和穆斯林学生时而会因伙食等问题发生摩擦。幸好埃塞俄比亚正教的信徒也不吃猪肉,否则矛盾就可能会更为尖锐。
1974年,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军人推翻塞拉西皇帝,建立了共和政体。厄立特里亚的局势并没有得到好转,内战持续多年。同时期,埃塞俄比亚连年闹饥荒,死去近一百万人,终于不得不于1993年承认厄立特里亚独立,失去了唯一的海港马萨瓦。两国边境至今仍然关闭,埃塞俄比亚目前海运物资要靠已然从法国独立了的吉布提用铁路转驳。

喜来登酒店窗外所见的亚的斯亚贝巴市貌(2010年)
上世纪9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推行社会主义的军人政权垮台。现在埃塞俄比亚实行从西方引入的议会民主,但是并不顺利,大选之后往往需要由西方观察员判定选举是否有效。
艰难的现代化
从我初识埃塞俄比亚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当初少不更事的青年如今已是满头银发。古老的非洲王国又怎么样了呢?带着这个疑问和几分怀旧,我于2010年1月从也门的首都萨那飞到亚的斯亚贝巴,接着又到贡德尔,共作了六天的探索。
刚下飞机就出了状况。我和许多乘客的行李都没有随人上飞机,因此要逐个填表登记,并被公司地勤人员告知:等候通知,行李到了再来机场认领。乘客对这种处理方式群情哗然,但谁也没办法改变现实。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在非洲其实颇有名气,在香港也常做广告。但是我在世界各地的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文明古国要想经营一家现代化的航空公司,绝不是买些新型客机,再培养一批本国的飞行员就能成功的;以客为尊的服务态度和地勤人员的素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
亚的斯亚贝巴的市容要比半个世纪前进步许多,但仍然难以和亚洲的任何大城市相比。我预订的是喜来登酒店,进去后却大吃一惊:这是我到过的最有气派的喜来登。听说是一个早年移民美国的埃塞俄比亚商人回国兴建的,刻意要把这家酒店打造成世界一流。因为当时非洲首脑会议即将举行,房间临时加价,要五百六十欧元一天!不过我还计划观光市区,不能只在豪华酒店里享受一流设备,所以第二天就转到另外一家相当一般的旅馆。
非洲首脑会议的主会场在中国援建的非洲统一组织大会堂。为了免受道路管制和被军警反复搜身,我没去参观。我选择去了国家博物馆朝拜人类的老祖宗“露茜”,又去了圣乔治大教堂参观了埃塞俄比亚正教的艺术,当然还免不了去找一家中国餐馆祭一次五脏庙。这家近年来新开的中国餐馆比我1963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吃过的中国餐馆要正宗许多,而相隔近半个世纪到非洲开创餐馆的两位老板的创业艰辛也就必然有所不同。
在餐馆里听说,中国正修建一条连接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铁路,也派有地质调查队;中国移动、华为等大公司在埃塞俄比亚有不少业务。在路边的地摊,我随手拿起一个很薄的塑料盘子,翻过来一看,原来也是Made in China。
古都贡德尔的市区扩大了许多,还添了一两家挺不错的酒店,但很难说是更现代化了。毛驴拉车、尘土飞扬的图景依旧;小贩依然随处摆摊,人们仍是到处蹲着谈天。最明显的“现代化”是汽车多了,再就是男人大都放弃了长袍而改穿西装裤,多数人也不再赤脚,而是穿上了球鞋。
旧皇宫修复得还不错,卖门票的人能说简单英语。一群身上挂着导游牌子的人在入口处招揽客人,我选了一个中年男子。他的英语还不错,也颇为尽责地给我讲了一些历史和政治典故。但是他最希望我做的是第二天雇他陪着去(我当年曾经去过的)塔纳湖游览。我告诉他我已经在下榻的酒店订好了汽车和导游。他问我要付多少钱,我不肯说。傍晚回到酒店时,柜台职员告诉我,第二天预订的车子不能去了,旅游公司的经理稍后会来见我。晚饭时经理来到酒店,客气地向我赔不是,说如果我同意,他可以帮我找另外一辆差不多的车和另一个导游。我根本没有办法不同意。第二天早上7点钟,我依约到酒店大堂,只见头一天我在皇宫的那位导游笑盈盈地迎了上来:他就是我的新导游!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我真是服了这位地头蛇导游,也更加认识了在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确实很复杂。
我当然不会放弃一访我父母曾经工作过的医学院。它早已由埃塞俄比亚政府接管,规模扩大了,但依然十分简陋。我父母当年工作过的外科手术房和产科病房的外貌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外面焦急地等候消息的病人家属和四十七年前几乎是一个模样,令我不胜唏嘘。到了院长办公室,我递交名片,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能和院长打个招呼,秘书抱歉地说院长到亚的斯亚贝巴开会去了。她礼貌地邀请我到学院会议室兼院长会客室参观。会议室墙上挂着一排照片,其中赫然有家父当年的两位上司——医学院院长和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主管的照片。家父去世已近二十年,想来这两位比家父年长的院长和主管也已作古了。
家父母当年从台湾到埃塞俄比亚辛勤协助开创的医学院,这些年来的进步似乎不很明显。对比我和妻子1990年从美国回香港参与创建的香港科技大学,如今已是人才济济,枝繁叶茂,不禁感到一个社会的发展总趋势往往是个人事业成就的最主要因素。
埃塞俄比亚一向是傲视非洲之角的雄狮;它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它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在这样的地理和人文土壤上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的确十分艰难。回想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观诸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从非洲之角东望华夏神州,我也颇有感悟。

贡德尔郊区市场一景

埃塞俄比亚西北部小镇一景

在贡德尔大学医院病房外的病人家属(2010年)

世界卫生组织在贡德尔租用的宿舍(作者父母曾在此居住)